
刘宝怡是大哥的孙女儿,假期她当老师的姑姑把她从广州带了回来,她已经三岁多了,可我就见过她一次,那还是她刚生没多久,随她父母回来看望她爷爷奶奶。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已经三年过去了。那天,我专程到哥家去看她,她坐在书房内宽大的靠背椅上,看着电脑上播放的动画片,看到我进去,她好像看到了久别的人一样,欢笑
大哥今年六十一岁了,他是家里的长子,从我记事起,大哥好像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说话落地有声,因是老大,母亲多多少少有点偏袒他,再加上他十九岁就离开家,到山东当兵,在入伍的第二年,因急性肝炎而离开了部队,当时是母亲带着刚学会走路不久的我到部队去看望大哥,因大哥患的是传染病,我是不允许进去和大哥近距离接触
又是周末,卢小凡站在空旷的校园里,校园内到处静悄悄的,该回家的同学和朋友都各自回家了,只有她,落寞的站在空无一人的宿舍楼前面,低着头,用脚踢着不知谁丢的一个空易拉罐,空易拉罐在空旷的楼下发出有点刺耳的声音。暮色开始笼罩起四周鳞次栉比的楼房和高高低低的树木及校园四周的绿草坪,冬天的风很硬,卢小凡缩了缩
夜已黑那盏灯已经点亮照着你迟疑的步履不要迷路你知道那路的尽头有人在翘首遥望苦苦等待别彷徨那盏灯灿若夏花照亮你孤寂的心扉给你的钥匙别丢那扇紧闭的门需要你去开启它等待着那束阳光2012年2月29
今夜没有月等你,在寂静的春晚时间在流动你的灯没有亮真想问一句你今天还好吗累吗但矜持不能让我开口静静守望着那片天空我沦陷在你的城池夜已深没有月等你,在霓虹闪烁的夜晚时钟在敲响你始终没有出现真想问一句你回来了吗高兴吗但我不能对你开口默默遥望着那片天空情感在忐忑中飘摇……2012年4月7日
小药商并不小,大概三十几岁,他的儿子已经三四岁了,只因为个头小,大概一米五左右,在男人中已不能算是几等残废,完完全全算是侏儒了。因为是医院,医药不分家,药商虽然让老百姓恨得牙痛,政府也在不停用高压线打压,但药商这个行当还是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也许是它的高利润和轻松,让这个行当惹得人眼红而后继力量雄
是你吗那有点古怪、调侃的语调让我疑惑往昔那谆谆嘱托萦绕心头、凝聚无限温暖的叮咛此时好像远去……是我,是我你辩解着开始担心我的疑虑你叫出了我的名字又讲了只有我知道的数字哈哈,我们像特工彼此竞约定了暗号想着你轻轻呼唤着你阳光流淌进来抚慰我雪藏的心房、为我疗伤静静遥望着你在的城市幸福在我心里泛滥惑在这里解
邻居去年楼上搬来一对老夫妇,男的姓童,大家都叫他童大叔。童大叔大概有五十多岁的样子,矮矮胖胖,左半身有点不灵活,是因脑溢血留下的后遗症。每天我上下班在楼梯间总能碰上他和他老伴儿。他上楼的样子很艰难,像一两岁的幼童,两只脚要全放在同一台阶上以后,另一只脚才能抬起来再上第二层台阶。他的老伴儿总是先上到楼
上班路上,总经过一家做汽配生意的店铺。店不大,里面大大小小堆满了各种形状、黑乎乎的零件。经营店铺的主人,是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好像在讲述着岁月的沧桑。他不爱笑,看人时眼神有些犀利又含着严肃。咋一看,像是一位不懂生活情趣、只知埋头干事的单调男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判断他不懂生活
这天王小娇又去参加总校召开的一个宣传会议,她在分校任宣传科科长。每年一度和总校一起的联欢晚会她总是策划人之一,今年也不例外。王小娇毕业于华师师范学院音乐系,也许同艺术打交道,人也显得比平常人多几分飘逸和浪漫气息。虽然她已是位十二岁孩子的母亲,但身材的娇小、白皙圆润的脸上镶嵌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使整
傍晚,站在窗前,端着一杯茶水,看着遥远的马路上人来人往,步履匆匆,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吴桂林”的叫声。“吴桂林、吴桂林”我在心中默念着这个的名字,它好像一下复苏了我遥远的记忆……一个身材瘦长、白净的脸上布满雀斑的一个少女的脸呈现在我的面前,它拉着我的记忆,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岁月——那是我的儿时玩
我的第一双高跟鞋是刚上初中那年,姐到外地学习给我带回来的。因为是第一双高跟鞋,所以对它的印象就特别深刻。记得那时,当姐从提包里掏出一双浅棕色绒布面、上面镶嵌着许多银丝的黑色橡胶底的高跟鞋递给我时,我惊讶得睁大了双眼,既欣喜又忐忑不安。喜的是我们班甚至整个学校都没有人穿过高跟鞋;不安的是,穿上它怕会挨
三十一林枫正深深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忽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林枫的回忆,她抹了一把溢出眼眶的泪水,“喂,妈妈,今天晚上同学过生日,我在外面吃饭,不回去了!”电话那边传来女儿梦园的声音。“要早点回来呀!注意安全……”林枫的话还没讲完,梦园便着急的大声说:“妈,我知道!骑车小心一点,小姑娘一
二十林枫希望能从吴庆那里找到对陈子源案情有帮助的突破口,她幼稚的想让受伤的吴庆在办案人员面前说一些有利于陈子源的话,这样在量刑时会对陈子源有帮助。但林枫并不知道吴庆是一位刁钻、圆滑的人,而且还是个有名的无赖,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专门搞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在这次打斗中他的伤势并不是很严重,他心中也很清楚
灰色的、狭窄的水泥路面,无精打采的向前延伸着,路两旁没有一棵树、一朵花,只有一排低矮的楼房,仿佛是小巷灰色路面两侧突兀起来的障碍物。每次从小巷中走过,心中总会涌现出温暖的感觉,仿佛回到幼年时家门前的那条小巷,也很狭小、窄窄的很长,路两旁同样是一排低矮的楼房,只是在路边多耸立几根灰色的电线杆。小巷的春
孩子学萨克斯断断续续已经有三年时间了,每次到音乐老师那里上课,都由大人陪同,原因是人多车挤、乐器又重,怕孩子吃苦更怕不安全,凤里雨里相随,几年相伴,酷暑严寒中的漫长等待也不算什么,只要孩子认真学,投入练,心中也倍感安慰。今夜又陪着孩子上课,坐在黄昏后教室外面静静的走廊上,听老师吹着一首首悠扬动听的曲
我病了,病得很重,整个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能动。医生们在我旁边讲,说我意识不清,处在昏迷期,但具体是什麽病还需要做进一步观察,不能一下对我患的疾病下诊断。可很奇怪,他们说我意识不清,但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我都明白,心中也很清楚,就是眼睛和嘴巴不知为何不能睁开看和张开说。医生查完房刚走,我就听到护士端着
十一陈子源和刘嫣然分手后,便开着车回到自己那空荡荡的家中,他心烦意乱的和衣躺在那宽大的沙发上,闭上眼睛想着那天被林枫姐姐关在门外的情形……那年,林枫过年只值了一天班,其余的时间全部在姐家度过,并不是像姐给陈子源讲的那样“回老家去了!”那天,陈子源打来电话,林枫正在书房给童童讲数学题,听到姐接电话不耐
炎夏时节的十堰,人们被骄纵的烈日烘烤得不愿在外面多呆上一分钟,而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我却在感受着阳春三月的温馨和一派春意盎然的勃勃生机。坐在大巴上,汽车盘绕在滇藏公路上,透过玻璃向车窗外望去,让我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什么叫云海,淡蓝色的云缭绕在身边,我感觉自己好像坐在大海的快艇之上,周围是无边无际的苍茫大
一已是早上八点钟了,刘岚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翻了个身,抱着一个大大的软枕使劲贴住面颊,仿佛还想睡一觉,但突然一骨碌爬起来,把被子堆在一边,坐在床上睁开双眼,她一下还不能确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已经醒来,朦朦胧胧中感觉自己好像刚刚和父亲在争吵。她环顾着房间,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她努力回忆着,才猛然想起自
 小鹏P7+:全球首款AI智驾掀背轿跑,11月7日荣耀上市,预售价 20.98 万元起
小鹏P7+:全球首款AI智驾掀背轿跑,11月7日荣耀上市,预售价 20.98 万元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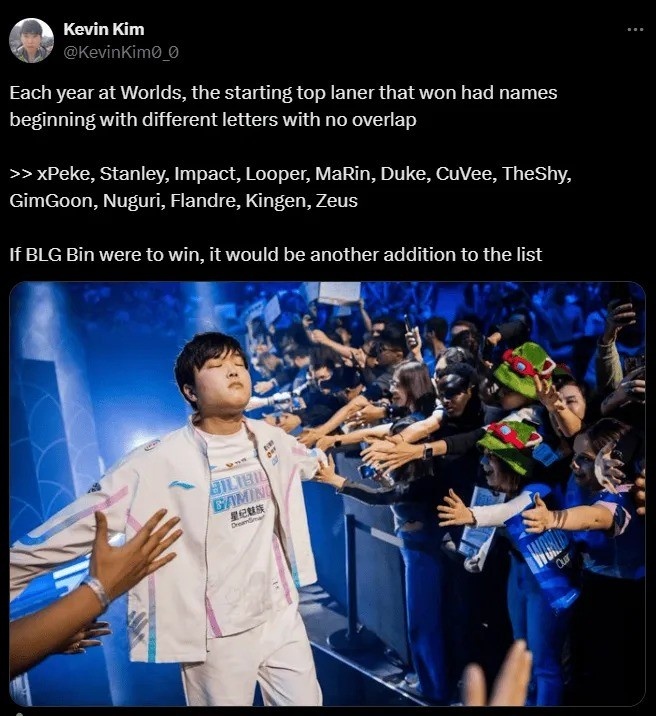 历届S赛冠军首发上单首字母均未重复,若BLG夺冠则新增B开头
历届S赛冠军首发上单首字母均未重复,若BLG夺冠则新增B开头
 车企冲刺年度KPI?全新别克GL8等17款重磅车 11月上市新车抢先看
车企冲刺年度KPI?全新别克GL8等17款重磅车 11月上市新车抢先看
 爆料人:iG的新资方有实力,但是问题在于,就差校长点头卖了
爆料人:iG的新资方有实力,但是问题在于,就差校长点头卖了
 “小路虎”来了!新款瑞虎7 PLUS和瑞虎7高能版将于11月1日上市
“小路虎”来了!新款瑞虎7 PLUS和瑞虎7高能版将于11月1日上市
 LPL官方预告决赛解说主持:Yagao作客评论席为前队友应援
LPL官方预告决赛解说主持:Yagao作客评论席为前队友应援
 主持余霜晒照:和老公泽元一同漫步街头 走走看看好不快活~~
主持余霜晒照:和老公泽元一同漫步街头 走走看看好不快活~~
 体验雷神 EM-i 超级电混 银河星舰 7 百公里油耗实测
体验雷神 EM-i 超级电混 银河星舰 7 百公里油耗实测
 余霜分享半决赛记录视频:世界赛总有熟悉的人在身边
余霜分享半决赛记录视频:世界赛总有熟悉的人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