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至今日,集中供热的暖气已经司空见惯。我却依旧对熊熊燃烧的炉火情有独钟。火焰和色彩及光亮,永远留在我记忆中。记得小时候的冬天,农家几乎家家生火炉。用干柴和碎木将火引燃,然后再加上玉米蕊、花柴梗等耐烧的柴禾。红通通的炉火便燃烧起来。火炉子有的是石盆,有的是泥盆。我家的火炉是父亲亲自动手做的,一个破铁盆
家住七楼,一个和泥土喧嚣无缘的高度。我却偏偏是个颇注重情调的女子,为了我的那些花呀草呀的嗜好,老公和我硬是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将一个花池建立在我家的阳台上。花红叶绿,鸟语花香,万紫千红,姹紫嫣然,阳台成了我家最美的风景。不知何时,蟋蟀这群不速之客也光临了。初闻它们的叫声,我特别兴奋——居住在城市竟能
曾经因为父亲是一个普通又老实的农民而自卑过;曾经因为同学有一个博学多才的父亲而羡慕过。我常常在感叹别人有那么优秀的父亲之余生出对父亲的怨恨:父亲,你为什么就不能让女儿为你而自豪一次呢?大学毕业后不久,我从原来的一家杂志社跳槽到一家广告公司。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改变命运。虽然挣钱并不是我生活的
荒春四月,麦子还没有熟,而粮食已经吃得差不多。家家户户开始吃红薯面,吃榆钱,吃槐花,也到田野里去找野菜。因为我家人口多,粮食少,是村里的缺粮户,印象中总是饿。大人们因此常说:“荒春,荒春,饥一顿饱一顿。”而我却独爱四月。因为在这个遍地油菜花黄的季节,地里的豌豆角也饱满了。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煮蒸着吃。生
小时候,母亲总是说我和弟弟投错了胎。他安静腼腆得像个小女孩;而我则风风火火,简直像个假小子。一大群穿着开裆裤的小伙伴总是跟着我在村里四处乱窜。每到一处总是闹得鸡犬不宁。一次看到村里唤做“四哥”的人脸肿得像个馒头。我们又好奇又好笑,围得他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起初他不肯讲,后来才说:“有本事你们去把老莲
推铜箍通常是男孩的游戏,但我们的同龄人笑笑却非常喜欢。笑笑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会推铜箍的女孩。平时笑笑总是推着她哥的铜箍骄傲地从我们的眼前走过,会推铜箍的笑笑令我们羡慕极了。笑笑只所以获得推铜箍的权利是因为她有病,好象是被叫做“羊羔风”。开始我们并不了解它的厉害,觉得笑笑和我们没什么不同,甚至她比我们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因为生活不富裕,每年我们上街的次数总是屈指可数。因此,对我们农村孩子来说,货郎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了。说货郎,其实往往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他们总是拉着一辆架子车,车子把上放着一个有木箱子大小用铁丝做成的百货箱,隔着货箱就能看到那些令我们眼花潦乱的货物。如五颜六色的花头绳、花花绿绿的豌
小时候理发,大都是那个被叫做王师傅的人理的。那时我们小孩都叫他“剃头匠”。他是一个40多岁的高个子男人,家住在我们相邻的一上叫做“布袋王”的村庄。每一个月他来我们村一次,除了像我母亲辈的妇女们是互相理外,整个小村的人几乎都是他理的。他来的时候总是挑着担子。一头放着盆子、板子、推子之类的工具;另一头则
那时候,我大约有六七岁,但这个年龄的我已经有了爱美之心。可是家贫,无法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一天,我看到哑巴的女儿群子居然扎了两根羊角辫。红色的头绳紧紧地缠在发梢,是那么的鲜艳夺目。使得长相平平的群子增添了几分光彩。羊角辫随着她的走动而一翘一翘地摇摆,仿佛在炫耀着它的美丽娇艳。群子用红头绳扎起的羊角辫
每到春天,到我家院子里勾香椿的乡亲很多。我家的香椿树是全村最大最高的一棵。高高的树干,茂密的枝丫。远远看去就像一把伞盖在树上。香椿叶又嫩又黄的时候,正能吃。凉拌、配鸡蛋炒、和葱蒜掺在一起,成汁。不管怎么做都能吃出它的香味来。乡亲们都爱吃,常到我家勾几片叶子回去当菜吃。人缘很好的母亲总是有求必应,就好
每当我看到牛,总会想起童年的伙伴子向。他特别喜欢骑在牛背上玩耍。谁也没想到牛背会是他走向天堂的最后一站。距今将近20年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火烧云的下午,一阵哭天喊地的声音从七奶家院子里传来,人们都纷纷出来看究竟。只见七奶坐在地上双手不住地拍打着大腿:“子向娃,我的子向娃,你醒醒啊。”躺在旁边凉席上的
春天的时候,一群群鸭子鹅在水中快活地游来游去。岸边的柳树吐出嫩芽。我们常常在放学后上树掰柳枝。听大人们说,柳叶茶去火,柳叶晾干以后可以熬茶喝。其实我们那时是不懂喝茶的,农村的孩子不那么娇生惯养。饿了回家拿个生馒头就啃起来,渴了抱住凉水咕咕咚咚一通就算了事。我们找柳枝的主要目的是玩,用它来做口哨。找出
邻居家有棵杨槐树。树干很高,给我家的院子也罩了一片绿荫。阳春三月,槐花的香味飘进院子,使人忍不住朝满树洁白如雪的槐花多望几眼,吃槐花的欲望油然而生。因为和槐树的老主人三娘家是邻居,每年我们家也跟着沾光。槐花的美味令我老想起来嘴边还留下余香。三娘一共生了五个儿子,三男两女。在我的记忆里,那几年经常在三
我小时候最崇拜的人就是我们村小学那个梳着两个麻花辫穿着蓝布衣服经常微笑的乡村女教师了。因为她会唱一曲曲动听的歌。教学生唱歌的时候,她一边唱,一边弹风琴。她那有节奏的双手双脚和她领唱的歌喉,常常令躲在外边偷听的我们羡慕不已。听说那个会唱歌会弹琴的乡村女教师姓宋,还是我们村小学惟一的一名大学毕业的公办教
那时我们村的果树并不多,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在村子里闲窜,对村子里的果树了如指掌。算起来还算数枣树居多。能称为“枣树之王”的大概要数我大伯家门前的那颗歪脖枣树。听说歪脖枣树是我老爷年轻的时候栽下的,大约有百十年的历史了。树不算高,足有腰那么粗。每年能打枣上百斤。从枣树开花开始,我们一直盯到青枣变红。有
牛屋已经变成一堆废墟。站在曾经是牛屋的废墟上,我怅然若失。当年的牛屋在现在看来就好像一所幼儿园。乡村孩子的启蒙教育就是在牛屋里开始的。牛屋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人就是五伯。他是我三爷爷的长子。据说五伯年轻的时候很聪明。当初我那在县城里当文书的爷爷还把他当作重点培养对象,以便光宗耀祖。同样因为五伯太聪明了
在我童年的乡村,一般是没有电影院的。能看的只有露天电影。有时是办红白喜事的人家请电影,有时是村里出钱演电影。看电影是我童年时候最快乐的事。每逢这时,村里的大人小孩就像过年似的兴奋。在那个信息闭塞的乡村,我们对外界的了解全凭电影。电影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黄昏的时候,演电影的来了。他们骑着自行车,车子后
“冰糕,冰糕。”随着一声声稚嫩的声音望去,就会看到一个推着破自行车的卖冰糕的少年。这是我五六岁时在农村经常看到的。天气越来越热,卖冰糕的越多。当然天越热,人们才会奢侈一回。卖冰糕的生意自然会很好。我的堂哥明齐便是卖冰糕中的一员。明齐哥从小就表现出做生意的天赋。和二伯父一起上街卖菜还大声吆喝招拦顾客。
我所居住的小区位于城市南郊。不远处有一座绿树掩映的村庄。它与我童年时期老家的村庄很相似。常常在黎明时分,被相似于老家的鸡鸣声从梦中唤醒。这使我就会想起母亲,想起遥远的关于童年的往事。读小学是在一个叫做“黑张”的村小学。因为需要晨读,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当时家里没有钟表。鸡鸣就是我上学的钟声。乡村的夜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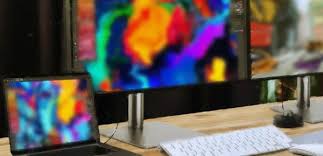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