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认识一些人,这些人都应该是这个世界一种平凡的存在。我留在他们中间的年华,都是这些年这个世界对我的塑造。我确实有很多光怪陆离的梦,说起来大抵是一些骚情而伪文艺的念想。比如我想在我下一个生日之前,去西藏,看海子。比如我想坐很远的火车,穿越很多个黎明和黄昏,去见你,一面。其实,我只是不想把自己不年轻的生命浪费在一个地方。这些念想成为我游荡在这个世间的外衣。所以荒诞不经的是我的梦,而现实里,x丝才是我的
我住在一个镇街里,去另一个镇街看你。这中间隔着山,隔着水,隔着云和雾。我是在秋天的雨雾里出发的。在出发前的晚上,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种我们相见寒暄的方式。我觉得有礼有节的应该是这种:嗨,好久不见。我回来了。然后我轻轻走向你,给你拥抱。仿佛我们认识很多年。松开的时候,我应该不会掉眼泪。掉眼泪是文青做的事。我只是个普通青年,用普通平静的方式去与你相见,和你虚度一个下午的光景。这种方式,
从前你喜欢一个人。她不喜欢你。你还是喜欢她。你决定等。春等不到,就秋。秋等不到,就冬。冬等不到,就白头。她喜欢别人的时候,你还在喜欢她。慢慢地,慢慢地你们没了联系。慢慢地,慢慢地就过了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你突然发现这TMD不是喜欢。这是爱。因为这个世界很大,人活在其中,很容易"失联&qu
还没做好准备,我已经在路上了。转山,转水。仿佛一次一次的轮回。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车转。水是金沙水,山是玉龙山。山,要伸着脖子,仰着头颅方能看到山顶,方能见着山顶的雪,和云彩。水,要侧耳倾听,静下心思方能知道它归向何处!海拔1800,2300,递增到3000多的时候,开始有稀落的村寨,和白云深处的
前些天,大哥跟我说了,你闲着,还不如早点回家去,再过几日,爸就过生日了。在这以前,同乡的叔伯常常认不出我是谁家的孩子。一说我父亲的姓名,便连声惊讶。问我父亲多大年纪了。我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四十八岁。如同别人的青春永远十八岁一样,我父亲的青春是四十八岁。四十八岁的你头发青然,筋脉突起,喝酒如牛饮水
很多年前,葛大爷在《甲方乙方》里,深情的道:“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2013年就要过去了,我也很怀念它。这一年里,我很好的朋友找到了自己的土壤,盛开如花。心有幸福守望着,真好。这一年里,我亲爱的父亲已是天命之年。那些属于他的岁月已沉淀成手掌里的纹路。峥嵘曲折,却始终握在他的手里。他的手掌始
“十·一”了。平常年份,这个时候是最忙的。然今年国家的新政策尚未正式实施前,各种传闻已让市场风声鹤唳。现在落得散淡萧条。无奈只得横亘在房间里,作罢。眼瞅着别人:能飞机的都飞机了,能火车的都火车了。能汽车的都汽车了。心里难受死了。一帮孙子早已聚在新的据点。在秋天的操场上打着篮球。哈头哈脑互喷球技。在篮
儿子妈妈祝你生日快乐没有标点的停顿:儿子妈妈祝你生日快乐。妈,你送给我的礼物。我收到了。妈,你把爱这个字藏在“儿子妈妈祝你生日快乐”这串摩尔斯密码里了。妈,我长大了。这串摩尔斯密码,我读懂了。短短的十个字,读了好几遍。眼泪早已开花了。手也抖得不行。“谢谢您和老爸20多前给了我生命。您们辛苦了。我爱您
在我记忆里,镇街旁边曾有过满野的油菜花。一丘一壑的。那会儿,走在田埂上,风里都是油菜花的味道。你常同我玩迷藏。突然从油菜花地里蹦出来吓我,满头满脑是俏皮的汗珠,细碎的花屑和清淡的芬芳。很多年后,我忘了你的名字,却记住了这个场景和这条镇街。不过你疯起来的时候,真的有风吹过来的感觉。还好,我也记住了它。
国庆至,恰逢律法出,吾辈初入世谋生而遇之。光景惨寥,左突右奔。困之。无奈便见山涉水,作一闲心淡泊之人。以消寂寥。久之,山水之于我,亦如我之于山水。恰我心造日月,便有了日月。今驾乌篷,又上南兰章,临水照影,垂钓娱情。曾系乌篷南兰章,一杆垂钓碧连天。闲在云间作野鹤,临渊羡鱼不羡仙。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哥已很难得管母亲叫妈了,而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叫老太太了。可能我老哥已经从儿子的身份里转变过来了。做了父亲,有了妻子,有了女儿,有了自己小小的家。他这样老太太来,老太太去的。母亲倒真被他叫老了很多。可,妈。我也想管你叫老太太,好不好。这样叫你,觉着有如山似水的亲,连着血连着肉。
那会儿我们家西西还没学会走路,不过已经能沿着墙壁蹒跚了。她循着我蹬楼梯的声音,以为我父亲下班回来了。便一跺一跺地移到楼道口来迎接。见是我,退了几步,又摸着墙壁往回走。又返过头来怯怯地,警惕性地看我。“西西”,我刚伸出手想去抱她。她一急,小小的圆脸迅速缺了一块,“哇啦哇啦”地哭起来了。很明显,她已经忘
一三年三月。我出家了。没有为僧,是为生。以梦为马,独家出奔,跑到一个很靠近赤道的地方。不想透露地址,方位。不敢微博,邮寄明星片。不愿电话,简讯——给那些熟悉的人。其实,只想小心翼翼保留着苟且的潦倒糟落。不给他人看见我的糟糕。心里仅剩下小小的信仰:向着远方前进。独立陌生的生活。生活是离开了一个圈,又进
年前,给家里打了几通电话。总是父亲或大哥接待的。母亲总是避而不接。我是知道的,她心底里是怪我不回家过年的。眼瞅着我这般年纪,不好发作。终于有一回,她按捺不了。索了听筒,同我言语几句,便忽地沉下来了。我也竟无言无语。半响了,她方才唤我的乳名。又道:“你到底是不回家来了!”这语气分明是我小时候淘气时,她
假如我轻易告诉了你---她的名字那么就当我想念你了那么就请你看看星星终究有那么多眼睛也这样看你假如我一直没同你说---她的样子那么她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就请你好好活着毕竟你的脐带流着她的血液她火山似的沉默潜伏在你的胸口---爆发你有多老她就有多年轻如果你实在不懂得那这就是---孤独
圆席别宴聚复散,举杯容易再见难。饷醉不知云梦里,从此相忆已惘然。
寒暑三载,流水时光,春梦秋云,聚散容易。当毕业论文最后一颗句点,凝结成大学生活乐章里的休止符时,我开始我的收获感言。而在我开始一大串鸣谢之前。我的论文导师以专业、敬业的态度,让最后一颗句点,再飞一会。一会儿。所以就有了下面鸣谢的由来。在初稿既成,定稿未遂之间,我的导师,总喜欢在他炒股之后,利用他炒股
才见云霄火树开飞来流星万斛载一眼一眨美人目秋波暗送琉璃彩
岁经三秋凉夜自别后长寒日无言多常作枉思量
又有一些人好些时日不见了。朋友的身份逐渐模糊了。习惯长时间的不联系。突兀地扰人清乱亦是不好的。偶尔会想起一些细微的过去了事儿,时间之水洗涤不去的、留存下来的亦便是曾经了。曾某人家乔迁那当儿,2010年已然临近尾声了。多年靠蹭饭过活的她籍此感恩回馈,于是广施江湖请柬。悉数受邀前来的尽是恰当年的同学少年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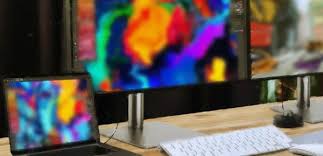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