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在擦黑时到了那座吊桥边。雨蒙蒙的落着。武元和金宝在桥底下的洞子里铺上一些麦草,把死者抬下车放在上面,玉桂坐在旁边,手抚摸着贵布满皱纹的脸,口里还在说着:“走,贵,咱回。咱回家。”金宝看着武元调转车头离开,他一个人跨过晃晃悠悠的浮桥,向村里走去。一群人表情复杂的看着他。他听见一阵窃窃私语。“贵回来了。”“在外死的人是横死鬼,咋进村呢?”“是啊,要从村子里过呀。”“真可怜!”“就是的。”贵的父亲拄
汽车在擦黑时到了那座吊桥边。雨蒙蒙的落着。武元和金宝在桥底下的洞子里铺上一些麦草,把死者抬下车放在上面,玉桂坐在旁边,手抚摸着贵布满皱纹的脸,口里还在说着:“走,贵,咱回。咱回家。”金宝看着武元调转车头离开,他一个人跨过晃晃悠悠的浮桥,向村里走去。一群人表情复杂的看着他。他听见一阵窃窃私语。“贵回来了。”“在外死的人是横死鬼,咋进村呢?”“是啊,要从村子里过呀。”“真可怜!”“就是的。”贵的父亲拄
在县城一栋白色的家属楼里,李副县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显得异常镇静。他一根一根的抽着烟,又不紧不慢的在烟灰缸上弹落灰烬。李广子从兄弟的神态中感到绝望的气息。“咋办哩?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的亲侄子!”“你说能咋办呢,哥。”广子从沙发上软了下去。李副县长没有看他一眼,起身推开窗子,冬日的阳光白苍苍地爬进来,像狗一样伸出长舌,舔着地板和墙壁。距离县城六十里的小镇上,尸体解剖正在卫生院里紧张进行。玉桂清楚了
连续几期要案使冀所长昼夜焦虑,一筹莫展。7.23营业所杀人抢窃一案如今已过去了近五个月,侦破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凶手仍逍遥法外。社会舆论一浪高过一浪,报纸上也公开指责。唐志平自动上报受贿一事,又使派出所的工作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已把不能迅速破案归结为无能和腐败。他明白自己的处境,再三恳请上级给他一段时间,力争在元月破获此案,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不算太完满的句号。凌晨两点,他接到电话举报李胜利殴
入冬的时候,丹江河就变得极瘦,满河滩卧着硬硬的石头。堤堰上的杨柳在有风的时候大呼小叫,在没风的时候便如针刺般直直的戳向天空。余晖给他们涂上一层薄薄的面霜没有清澈的积雪在山洼处泛出白里透红的亮光。几只暮鸦从岸边的老树下掠身而起,树枝不情愿的一摇,便有些灰色的羽毛在空里飘袅。暮鸦的翅膀融在落日里,太阳便被驮着向西山头飞去。西边的山像喝醉了酒,显现出潮红的血色。河水血红如泼,颤颤悠悠的晃水里的色彩搅动得
李胜利刑满释放回来时,惊讶于家中发生的变化。父亲腰板拘偻,母亲看了她半天才哭出声来。尤其是军利已娶妻生子,使他羡慕。他又回想起以前风风火火的日子。于是他第二天便召集刚在牢狱里结识的新朋和以前的老友聚会,光啤酒瓶就能拉一架子车。家里人看到他德性依旧,感叹要想改变一个人真比从猿演变成人还要艰难。下雪的那天,他豪情顿生伙同几位朋友骑上摩托、挂上猎枪上山打猎。落雪在车轮的碾压下发出破碎的声音。他们在两岔峪
米玲的病情仍在呈周期性的发作。这天她靠在床上,忧郁的眼睛望着窗外,寥寥的树枝上两片叶子在秋风里瑟缩。她出神地望着,想起了奥勒和特露法的故事,她痛苦的闭上眼睛,泪水很快的润湿了睫毛,顺着清瘦的脸颊流下。母亲背对她正把方便面撕开放在碗里,听到她喃喃的叫着“金宝”,转过身来,见她折磨的近乎麻木的神经又开始运转。她赶紧给米玲拭去泪水,解释说:“金宝会来的。他都来过几次了。你看这水果、方便面都是他拿来的。”
西京精神病院有着同一种医务人员,那就是富于宽厚和人爱,也有着许多不同的病人。在病房里哭的笑的打的闹得什么样的都有,金宝在也不觉得米玲的病奇怪了。他在病房里只待了一天,伯父便催促他回到小镇。父亲一下老了许多。好像人的老年只是一道门槛,他在不知不觉间跨了过去。小黄和雪儿得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便心急如焚的赶来。眼看着女儿的小腹已经显山露水,云霞不无担心地说:“这时候咋还能长途劳累呢?”雪儿揉捏着发肿的腿脚,
细雨飘荡在小镇的上空,是追悼会蒙上一层不同寻常的色彩。人群如水,无声的流成一条河。没有一把伞,一件雨披,大人和孩子都一同立在风雨里,任雨水淋湿他们的头发,在眼前滴落。今天他们将在这里告别一位亲人,奠祭一位年轻的英魂。地,县,镇领导和农行负责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李副县长主持了这次大会。武小兰、宋小惠分别被授予“金融卫士”的称号,并追认武小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员。会后当武小兰的遗体抬上车要去火化时,她的女
唐志平赶来的时候,现场已经被严密封锁起来。营业多周围挤满了人,他快步拨开人群,扑入屋内,一副惨象映入眼帘。“小兰——”他抱着她的头。她的头发被血液粘连在一起,发出暗红乌亮的光泽。“小兰!”他摇着喊着,想把心爱的人唤醒。然而她静静的,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白色的连衣裙上学记散漫。她像是躺在了鲜花里。“小兰啊——”他绝望的喊着。悲愤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她就这样的去了,身中二十余刀,脑后又受到重物的狠击。县
米玲在这个闷热的夜晚里因相思而失眠,她眼望着天花板,仿佛金宝会从那上面走来。这两个月来,她置身于爱的长河里,任凭着爱情的潮水一次次地席卷淹没自己。“米玲,我明天到你家来。”“行啊,你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行。”她天真的回答。“我是指正式来你家求婚。你同你父母商量一下,要是不同意,就在明早九点之前捎个信。”“不同意了还能捎信?”“那我来了把我拒之门外怎么办?”“不会。我父母肯定会同意的。我会给他们说的。”
大暑的这天午后,唐志平光着膀子在客厅里烦躁不安的走动,风扇旋转的热风把空气搅的更加沉闷。小兰还在睡着午觉。一个病怏怏的女人出现在她面前。“你是谁?”她问。“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妈。”“我妈早死了。你不是。”“我是。你再想想看。”小兰想呀想呀,突然间觉得妈并没有死。“妈——”她拼命的叫,喉咙却嘶哑的发不出声。再一看,妈已不见了。妈呀妈呀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孩子。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她胸前。她伸手一摸
飞絮若雪,飘袅徐徐,才落地,风又扶起,总不离人东西。看着父亲手掌不停地在眼前挥舞,飞絮顺风而动,俶尔远逝,往来翁忽,恰如轻灵的碟群。武金宝不由得扑哧一下笑了。“这鬼天气!”武占学嘟囔着。“这天气多好,不冷又不热的。”金宝又是一笑。占学折了个草棍蹲在地上剜牙,奇怪的看着儿子。武元过来对金宝说:“停电了。”“好”金宝顺口而答。“停电了机器就没法转。”武元又说。“不能转了好!”“不能转了还好?要停几天呢
初夏的一天下午,武金宝从山上下来走在雨后新晴的街道上,心情格外的开朗。洞子在掘进至238M处,突然遇到金含量极高的富段,贵凭着常年的洞采经验,立即令停工,并迅速地派人接武占学上来。接下来的一切近乎于神秘。工人被解散,武占学、贵、武元元、金宝四人在洞子里干了整整七天,吃近50M才穿过这段。矿石被立即袋装,让唐志平开着公安车秘密运到武家大院。所有的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武元又去重新招收人开采,占学说还
正月十五,金宝从山上回来时已是明月如盘,徐徐升起。村庄宛如披上淡淡的轻纱,影影绰绰地,看着令人心痛。一处一处的花炮,此起彼伏,争奇斗艳,呈现岀一片美丽的景象。有的伴着哨音,升至十几米高时突然一声脆响,炸出团五颜六色的斑斓,有的却席地而起,喷薄怒放。小镇的元宵之夜竟是这样的没哦!他径直到东庄。姐正在堂屋里把元宵一个一个地分开,姐夫在屋里给外甥女点起船灯。看着船灯,他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时代。正在想
这年的腊月,天空下了第一场雪。像是糊汤糂子撒了一地。武占学立在门前的大槐树下,在沙沙的落雪声里,心里充满了阴郁和悲哀。云霞坐在门前的小凳上,双手托腮,看着大院。天空灰蒙蒙的一片,灰的碾房、灰的树,这种色调把武占学也涂成灰色,显得飘渺而不真实。雪儿和小黄就是在这个落雪的早晨离开了这里,到小黄的老家陕北。小黄出院后,令人不解的调动了工作,治平追问了几次,他总是那一句话: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他拒绝
拍片的结果使人悬浮的心终于落地。颅骨没有损伤。剩下的问题就是吃药、挂吊瓶促使伤口消炎和身体尽快康复了。鱼的水千恩万谢。要是伤的是外地民工,他可能睬也不睬,但现在伤的是凤镇人,而且是丈人关系较好的占学叔的儿子,他就不能不慎重了。他甚至做出最坏的打算,必要时请丈人来说和。现在看来这一切读是多余的了。他慷慨的拿出1000元钱,却被占学硬是挡回。他便说过几天再来,让金宝安心养伤后就和贵一同上山了。“虽然病
广子回到家,军利已经坐在那里和他母亲叙家常。“胜利的事,你妈都给你说了?”“说了些。”“你着咋办?”“我哥那号人能有啥办法。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偏他整天还在混。人家混势、混龙头大哥哩,咱有啥办法。”“他再能还是我儿子。”“他拿你当老人吗?”军利反问一句,广子噎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问道:“你姐夫那里还好吧?”“能好到那里呢?他原来好说歹说让我去帮忙,我去了。他不常到矿上,即使去了也是看啥都不顺眼,发一
广子回到家,军利已经坐在那里和他母亲叙家常。“胜利的事,你妈都给你说了?”“说了些。”“你着咋办?”“我哥那号人能有啥办法。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偏他整天还在混。人家混势、混龙头大哥哩,咱有啥办法。”“他再能还是我儿子。”“他拿你当老人吗?”军利反问一句,广子噎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问道:“你姐夫那里还好吧?”“能好到那里呢?他原来好说歹说让我去帮忙,我去了。他不常到矿上,即使去了也是看啥都不顺眼,发一
广子回到家,军利已经坐在那里和他母亲叙家常。“胜利的事,你妈都给你说了?”“说了些。”“你着咋办?”“我哥那号人能有啥办法。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偏他整天还在混。人家混势、混龙头大哥哩,咱有啥办法。”“他再能还是我儿子。”“他拿你当老人吗?”军利反问一句,广子噎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问道:“你姐夫那里还好吧?”“能好到那里呢?他原来好说歹说让我去帮忙,我去了。他不常到矿上,即使去了也是看啥都不顺眼,发一
 免费漫画阅读站旧版官网-在线免费观看漫画全攻略
免费漫画阅读站旧版官网-在线免费观看漫画全攻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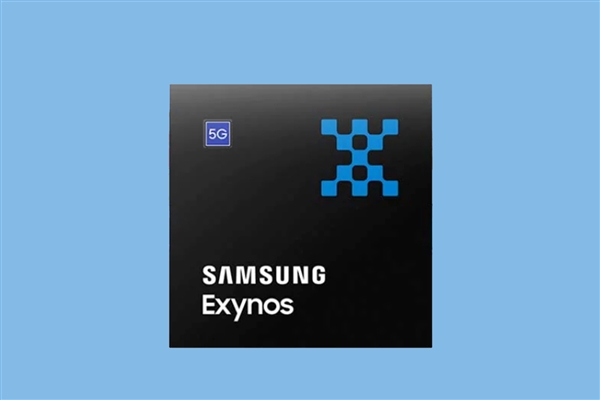 首款2nm手机芯片 三星Exynos 2600仅在韩国商用:无缘国内
首款2nm手机芯片 三星Exynos 2600仅在韩国商用:无缘国内
 小学五年级作文10篇【实用】
小学五年级作文10篇【实用】
 无畏契约契约怎么升级最快
无畏契约契约怎么升级最快
 七夕说说心情短语霸气
七夕说说心情短语霸气
 如何编译vs2010-vs2010编译教程
如何编译vs2010-vs2010编译教程
 小学四年级作文锦集(10篇)
小学四年级作文锦集(10篇)
 教师教学实习心得体会怎么写【5篇】
教师教学实习心得体会怎么写【5篇】
 元气骑士前传种植多久成熟-农场种植最短成熟时间预览
元气骑士前传种植多久成熟-农场种植最短成熟时间预览
 宝宝生病说说心情短语
宝宝生病说说心情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