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老家在一条幽深的小巷,宽大的四合院,中间有一株不知长了多少年的果树,自记事起,它就在那里,既不见繁密,也不见疏落,只在季节变化时,看出它的萧条。树下几把木藤椅,一个是桌被围在中间,经常会有蚂蚁爬满上面,偶尔也有毛毛中,只是它们的命运没有蚂蚁好。院子里有个淘气的男生,他会用火烧毛毛虫,然后还会把尸
一上午的时间结束了两科专业课,原来这学期又要过去了,可是我的意识还停留在暑假的安逸中。早上起来时得知,过三成绩出来了,赶忙去查一下,结果还好全过了。好是好,却高兴不起来。在这里,考过国三的都知道这成绩是怎么来的,就是拿到手这些证,也一样是白痴。大家有倒霉没过去的,都在担心下次的答案要是再不准的话,那
明天开始正常生活,加油!!!!昨天看了以前朋友写来的信件,很多贴心话如今再也听不到,而那些朋友,现今大多也是远走他乡,寻找生活了。有一位朋友说过一句话:以前走各级不久能看到的人,如今都远走他乡了,想想怪可怕的!我想也很可怕,不是走到美各方都有好友可以交的,要不怎么说知己难求呢!可是在返回来说,生活这
当我们年轻时,从不承认自己的幼稚,再慢慢成长蜕变之后,竟又发现自身如无知的孩童。于是啊,有些人狂妄,有些人沉默,他们忽视自身的缺点。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细腻的人。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有很多应有的情感淡化了,应有的印象模糊了。在仔细回忆时发觉,并不是淡化或模糊了,而是那些根本不曾实质存在过,就如同我想
得知阿杰有女朋友时,我又一秒钟的静默,旋即笑着说祝福的话。中午碰到阿杰,他说:我没钱了,请我吃顿饭吧。坐进食堂我们仍像一对情侣,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彼此的谁。最暧昧的时候也不过走路时拉我的手,揽我的肩,偶尔发条短信,称呼是老婆,内容却与情爱为无关。如果我能主动点,或许今天站在他身旁语气相依
再见到小唐时,我们已是成年人,开始懂得背负责任。我想笑,曾经故事中那些责任谁来背负呢?聊天时他说:现在努力赚钱养家糊口了。我们的故事发生懵懂的少年,那时的小唐时一个放荡不羁的男孩子,整日逃课,上网,喝酒,吸烟,打架。谁都不会想到乖巧的我会喜欢这样一个坏孩子,事实上,我真的爱他,义无反顾。那天,小偷把
当一个会说谎的人遇到一个不会说谎的人,不知道是悲哀的到底是谁,就像一个正常人对着一个傻瓜做一个傻事。我自认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并且说得极为不错,身边有人说我城府很深。当然他被我的假象迷住了,我一直在努力把自己装得像个深思熟虑的人物。其实,我很少能听得懂别人嘴里的声音,于是我打了一个“明白”的招牌笑容挂在
第一次,晓炎坐桌子,我坐椅子面对面聊天,还是高一下学期开学的一天。那时的她在我眼里是一个单纯干净的小女孩儿,我喜欢她俐落的短发,和湿润润的嘴唇。那天她第一次拉我的胳膊,要我给她讲寒假趣事。我就仰着头,一件件说给她听。开始她笑得很活泼,慢慢她没有声音,微低着头,乖巧的模样,让我不习惯。我就将笑话给她听
林林是一个长相平庸,身材矮小的女孩子,她特别羡慕那些有修长双腿可以和男生平视的女孩子。因为身材矮小,她受过很多委屈,当买衣服时,很多衣服都是因为没有那样小的尺码而与她无缘,尤其是裤子,对她来说简直是耻辱。所以,为了省事,她穿裙子。林林有好多条裙子,各式各样,高中低档的,无论冬夏,她都穿裙子。别人以为
曾经有一个男孩默默地喜欢我,就如同我同样喜欢另一个男孩。如果错位存在的话,这来那个份感情都会成功。可惜这两份感情重叠在一起了。于是,两个同样执着的爱情信念者,遭受了同样的伤害。都说爱情可以使人变得成熟,可我觉得谈爱情还远了点,不如说是感情吧,干净些。在感情作催化剂的年代里,我们加速了成长。也许成长是
阿木和音子是我故事中的主人公,我在思考如何叙述我们之间那段扑朔迷离的故事,就算到现在我都不知这一切是否结束了。音子说:“是缘分让我们产生交集。”她是我懂的友情后第一个友谊后第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们都倍加珍惜。而那时对友情最忠诚的表现是,将自己赤裸裸的呈献给对方。所以她告诉我,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开始注视它
男人叫龙,女人叫英,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让两个自由青年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逼迫。他们的爱情不被看好,婚姻也因为双方佳厅背景不同不被祝福。可是英毅然放弃良好的生活条件,投进龙的怀抱。婚后没有房子,英没有因为和婆婆小叔住在一铺火炕而气愤,她说:“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只要咱肯干,都会有的。”龙感激地将她揽进怀里
孤独的人,多半喜欢望窗外的风景,他们宁可凝视匆匆的行人,也不愿回头欣赏车内的温馨。于是遥远的孤独引领渴盼孤独的双眼,越走越远,走成一点。梦里总有很多事无法用常理理解,我还是一个不动常理的孩子,本以为一切都回原地不变,哪怕世事沧海桑田,而我们永远站在天际外面,是凝视一切的天人,可是转头之际你已背弃一切
学校死人了,寝室楼的水房里。没敢去看,听说是割腕。一个女孩,我认识的。那天消息传来时,我在画室,画板上是一个红红的苹果,鲜红艳丽的颜色让人有某种欲望。音子慌张跑进来,脸色苍白,语无伦次的说:“阿然,莎莎她---她---。”然后哇哭了出来,我问:“她怎么了?”“她---她自杀了。”“别--别开玩笑,你
不明白这样的感情算不算爱,认识了很久,有很多年那么久,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在一起,只是总感觉总差那么点火头,于是等来等去,等到现在谁也不愿在开口时,感情变的不确定。说不爱不可能,除了他再不愿看别的男孩。说爱,又不完全,爱的心情里掺进太多习惯和别的什么。很多时侯一直想写点东西,作为我们这段暧昧感情的纪念
很久不写字了,好象快忘记那种感觉,只记得曾有那么一段时间,疯狂的写,写什么不重要,重要是在不停的纸与笔的摩擦中,找到自己真实的存在.多久前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还没老去是记忆就疯狂的退化,有时明明已经长大,却误认自己还小,还可以,有权利做那些小孩子的事,于是放任自己为所欲为,再成人的世界,这种行为好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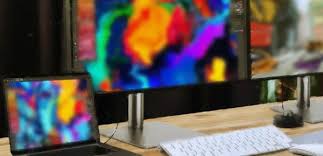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