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作者:索子(来自豆瓣)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40752484/写下这个标题让我有种既悲且喜的感觉,这个题目范围似乎过大,影射似乎过广,可同时又似乎太泛泛。但我想不到还能起什么名字,就这样罢。这段时间中国似乎很热闹——什么林心如、薛之谦一类黑料满天,然后是鹿晗公布恋情粉丝崩溃,都说娱乐圈没有隐私,对,它还没有边际,连我
前尘·方恪桐县很久不出粮了。自从方家从桐县搬走后,桐县就不出粮了。后来有人闲得慌,看田地都荒着,就在荒田里种了药,这才发现桐县的地种出来的药材要比同年份的其他地出的药材好,桐县自此改种药材了。桐县没了粮地,却有了药田,又是个富足的小县了。慢慢地,也就只有桐县的几个老人经不住儿孙们痴缠讲讲落满了灰尘无人接手的方家旧院里的故事。老人们讲到方家了搬离桐县就停下,说下次再讲后来的故事,孩子们听了这话便三两
长明街尽头的铺子开了。铺子名字倒是简单——长明街86号。且不说长明街的店铺人家没有门牌编号,就算有,这长明街满打满算也就16户人家,那铺子顶多算是个长明街16号。但铺子名全凭着老板的喜好,86号也好,毕竟人家就是起个长明街大号也轮不到别人置喙。总之,长明街86号开了。老板说要去云游去闭关,三年后,这铺子又开了。虽然,长明街的人也没人去关心铺子到底开没开。长明街的人家,都是怪人。铺子不做生意,人家没
一直很喜欢“本我”这个词,倒不是说有心像皈依佛门的人一样修行自己,这本我纯粹的无关信仰与向往,是出于无杂念的喜欢。说回本我。本我,我理解为原本的、固有的自己。追寻本我,大抵是希望离开人世的自己同来临尘世的自己一般纯真、干净。而一般来说,能守住而且回归本我的人,多是心性坚定或是历经沧桑的正直之人,那些被尘世埃土浸染的面目全非的人,是从一开始,就失了本我的人。守,一直以来,都是一件难事。千古江山、百万
我已记不清后悔反思过多少次了。每一次都被愧疚所缠绕,说好每个下一次要克制与正确处理,但每个下一次都只是在告诉自己再下一次。没有下一次了,关于个性,再没有下一次了。弟弟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贪玩、任性又不听话,这让人气恼——总会很气恼。于是在他做出些在我看来出格的事之后就会觉得他很不对,很不听话。而多次劝说无果后就觉得这真是个让人劳心伤神的存在。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每每弟弟犯下以前也曾犯过的错时,心里
从此以后,就真的没关系了。我从那个新开不久的咖啡店走出来,扯扯让浑身上下都难受的齐膝连衣短裙,看着左下角因变了形而与众不同的几朵碎花,忍不住笑了出来。我的第一次淑女风范,还是成功的。笑着笑着,就流下泪来,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能向我递来帕子的人。而我,也不会再接受了。在我年轻的时候,瞧,说得好像我有多老似的,其实我还年轻,脸上有精致的妆容,化妆品是店员一边羡慕我白嫩皮肤一边夸赞后推销来的名牌。
花开在花园里,树长在专门留出的坑里,草生在没有水泥彩砖的地方。所以我应该在学校里,教室中,座位上。书还在那里放着,习惯性地翻在一定的页数停下,后来的知识点和考点,一直在等下次再看。笔袋里的笔换过了第二茬,从里到外都是崭新的感觉,终于没有“用腻了”的感觉困扰自己。把每一本书和每一张卷子都打开过,粗略的看看后又收起来,胃里是突然翻腾起来的不适,动动笔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春天和秋天都过去了,只是一年还未
我正满心欢喜的做着晚饭,饭菜的香味混杂着空气在我身边起舞,于是身上每个细胞都叫嚣着饿了。我咽咽口水,看着锅里不知忧愁地打闹着的菜,隔着热气冲他们长叹一口气——父母都还没有回来……我正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停下动作,等等他们,门就开了。父亲看着屋里的情况,脸上没有笑意。“***去世了。”他红着眼,脸颊被风吹得通红,鼻孔隐隐收张着,语气沉重着。我一时没能反应,手里还握着铲子,上面有些斑驳的菜汁
醉剑卧莲,石枯水浅,叶荷眉梢尖疏影戏月,云淡风轻,星夜天光外独坐抚琴,音思漫缭,日暖风萧瑟醉里挑灯,烛火明灭,月明星寂寥
这些话,或许条理不清,或许颠倒反复,但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些话,我还不会告诉你。原来我总会奢侈的穿过一片草原——在回家的路上,经过让胃液翻腾的长长的盘山公路,就看到两边青葱的草原。这么多年,我终于接受了这条反复修缮过的路。——即使我无数次在这条路上呕吐吹风。每隔一段路就会有穿藏袍的妇女裹着粉红色的头巾站在风中,身前或身旁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零零散散放着几个或红或紫的小塑料桶——无论是人还是桌子,
因为还爱你,所以会悲伤。从来没有这么悲伤过。‍我没听到开门的声音,所以觉得猛照射进来的阳光太刺眼,让人想到落泪。我没有动,但我正在努力压抑着自己的呼吸,好让隐隐约约的脚步声清晰些。即使那人迟早会来我眼前,但我还是想早些知道——知道那人是不是我心中所想念的、唯一想念的人。是,我会伤心;不是,我会更伤心。从来都没这么悲伤过。我已经很少想起你了。这是第十五天。晏安,黄小仙走出失恋需要
秋天已经来了但听说别处下过雪了这里的早晨看得到薄霜许多叶子都变了色红的像火,黄的像阳站在清晨不冷不热的阳下远远瞧见高处杨树叶飘落但它们还是绿色的我早已不再是你认识的我四季就在这之间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我处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冷风从远方来到我身边就像忽然发现秋已来
一月,我抬头看到忧郁的蓝天雪覆盖的地方都是思念二月,我背起行囊挥手作别这地方风吹过的地方都是冬天三月,我站在渐暖的阳下看着你想说的话堵在心里说不出四月,我大着胆子牵你的手你没躲开,我也没放开五月,我是天生的苦行僧注定无法在这尘世间驻足六月,花都在路边花园里寂寞无声的绽放着七月,我去了远方看流星等了一夜只见到阴阴的天空八月,在夏季的尾巴上荡秋千我在翠林里听到我的笑声九月,我在街上看人来人往那一瞬间,
在这片灯光下,我骑在车上,听到了孩子们的欢歌、大人们的笑语。我没有停下,只是想随他们笑一笑。然后我就走远了,再听不到欢歌笑语,那片灯光却更亮了。姐姐出嫁那年,我应该算是不大不小的年纪。我觉得,我该是个十岁左右的姑娘,因为我可以去送嫁——穿上新衣服,梳上翘辫子,在闹新房的时候捍卫还是女孩的新娘——要知道,这对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是极大的荣耀,这不仅仅表示了你与新娘的关系匪浅,还意味着
他还想抱抱我,用那饱经沧桑的双臂,揽住他长大了的女儿。轻轻拍着她的肩膀,说“一切都好”。父亲的脸庞是黑的,又透着被晒伤的红色。那些都是高原上的太阳并未给如洗蓝天下拼搏的人们留情的印记。父亲的双手上结着厚厚的、褐黄的老茧,摸上去很硬、很硌手,但我还是喜欢握着他的手,那里满满的,都是暖。父
我在远方听海声,用隔了山水重重千里迢迢飘渺海声,平复着我日日夜夜为山那边而躁动的心。我在窗前静坐,看见窗外孤星渺渺在天际。无风无月的夜里,星星也寂寂在看不见的远空,这种夜,成了我最喜爱的时刻。在一片静的暗里,就好像天地间只剩我与夜默默相对。等一切声息都混在我的呼吸里,我就像成为精灵,从耳朵里迈进那么
“来年春日,晚歌,等来年春日,我便禀了父亲向你提亲。”少年瞧着一心在秋千上轻荡的少女,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却也未恼,只是说完话就轻笑着看着少女。少女许久才回过神来,看着不远处倚树轻笑的少年,红唇嘟起,一双大眼里尽是想到趣事的欢悦。“陆均啊,我想去看看那个出了名儿的妓子,你陪我去吧!”说着,跳下秋千提了
你存在,在我之外。我一直像只斗兽一般,用尽全身气力挣扎着,想要逃出牢笼。我每日沉溺在枯燥的题海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看着窗外,人来人往,车如流星一闪而过,蜿蜒的山脉隔去重重思绪,于是我便想要逃离,无论哪里,无论为何,只要逃离就好。不在乎远近与路途。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我才不愿做个乖学生,我才不愿庸庸碌
这是一封情书,我怀了希冀与忐忑落下笔。看笔尖倾泻的流年,小心翼翼地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爱恋心事。我踌躇良久,徘徊者、彷徨着,久久,还是用轻颤得手握起笔。我有多么用力呢?用力到指尖泛白,笔尖划破几张纸却不过落下寥寥几笔。你一定不知道吧,我在你不知道的地方,看着落日悲鸿都渐渐消失,看着远方重重山峦隐在黑夜里
当有天,内心里住进怨恨,而原本就在的怯懦并没有像说好的那样退居在角落里,而是更加肆无忌惮的掠夺更多位置,当它触及到怨恨时,于是心里无处可供发泄的不知名火焰就开始更猛烈的烧起。心被灼热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仿佛时时刻刻被千万只虫蚁噬咬着,手心、腕上开始感到不能驱逐的痒,折磨着自己不能有一刻放松。痛苦地寻找
 Deepseek搜索时如何查看更多相关结果-Deepseek搜索怎样查看更多相关结果
Deepseek搜索时如何查看更多相关结果-Deepseek搜索怎样查看更多相关结果
 帧数助手如何做任务-帧数助手做任务的方法
帧数助手如何做任务-帧数助手做任务的方法
 POKI免费游戏入口 无广告秒玩直达
POKI免费游戏入口 无广告秒玩直达
 剪映hdr开启好还是关闭好-剪映hdr开启好还是不开启好
剪映hdr开启好还是关闭好-剪映hdr开启好还是不开启好
 Safari闪退如何修复-Safari闪退怎样解决
Safari闪退如何修复-Safari闪退怎样解决
 崩坏星穹铁道全角色遗器推荐
崩坏星穹铁道全角色遗器推荐
 REDMI Turbo 5 Pro最快春节前亮相:首次搭载天玑9系芯片
REDMI Turbo 5 Pro最快春节前亮相:首次搭载天玑9系芯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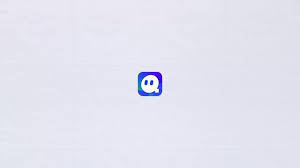 小木虫如何注销-小木虫怎么进行注销
小木虫如何注销-小木虫怎么进行注销
 汉字找茬王喇找出15个字攻略详解
汉字找茬王喇找出15个字攻略详解
 汤姆猫炫跑游戏玩法攻略-汤姆猫炫跑官方正版入口
汤姆猫炫跑游戏玩法攻略-汤姆猫炫跑官方正版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