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江依然如故地流着。夏季,两岸郁郁葱葱。雀坐在岸边的石头上,两眼痴痴的望着江中驰过的轮船,傍晚的阳光在她的眼中就像维送给她的玫瑰花,阳光下的柳树就像玫瑰花的叶子托着太阳。江水一晃一晃的,把雀的心晃得七零八乱。雀认识维是在去车间送通知的时候,当雀飘进车间办公室时,见车间主任不在里面,准备出去,突然,从办公桌下面拱出一个人来,用袖口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冲她笑了笑,大步走了出去,刚出门又扯了回来,把雀吓
5月10日星期日,女儿买了一支康乃磬送给她母亲,我这才知道今天是母亲节。翻了些许书,便知道母亲节的来由。梁实秋先生在《西雅图杂记》这篇文中写到:“美国报纸上有一则短文,标题为《妈妈难得休息一天,纵容她一下吧》。一位母亲躺在床上吃早点,由丈夫和孩子们伺候,那便是母亲节的礼物,如同稀奇的珍宝一样受人欢迎”。其实,一年当中被纵容的一天,也怪可怜的,何况这一天丈夫的孩子在厨房里乱得一团糟,不是烧焦了锅,就
2005年的端午节上午,我从单位回到老家,看望父母。走到前坪,看见偏屋台阶上站着一个老人,我一惊,以为外婆站在那里,可外婆已经去世一年多了。走近一看,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个子不高,稍微佝偻的身上一身浅蓝色衣裤,花白的头发朝后梳得整整齐齐,面色红润,笑容可掬,一脸慈祥的望着我,我疑惑的对她笑了笑,看见妈妈从堂屋出来,接过我手里的东西,对我说,这是李娭毑,现在住在我家里,并对李娭毑说,这是我儿子,
雨后、傍晚,战场上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炙热。卫生员素英搀扶着一个头部受伤的士兵,跟着担架部队往山下后方撤退。天渐渐暗黑下来,只是偶尔传来一两声零星的枪声,烧焦的树木和石头黑魆魆的,越看越鬼魅。地上不知道是敌方还是我方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的躺着,流着的雨水混合着血水积成一洼洼的水潭,踩上去黏糊糊的,让人恶心。突然,两声枪响,士兵啊了一声,身在晃了晃,依着素英的身体慢慢的滑了下去。素英恐惧得大叫一声,被
一鸟和蝉夏天,鸟妈妈和鸟爸爸在树上筑了一个巢,一起轮着孵化两个鸟蛋。一天,树枝上来了很多蝉,整天吱吱大声叫着。鸟妈妈被蝉声吵得睡不好觉,就时不时去驱赶蝉。鸟爸爸说,你这么不安心孵蛋,对孩子们有影响的。鸟爸爸孵蛋的时候就不去驱赶蝉。它知道半个月后,蝉的生命周期就结束了。鸟爸爸外出觅食的时候,鸟妈妈一直不安心,常常去驱赶蝉。28天后,其他鸟的孩子都出生了,而鸟妈妈的孩子没有半点动静,全都夭折了。鸟妈妈
外公是一名木匠,一位技能高超的手艺人。我几岁的时候,住在外公外婆家。那是条河的旁边,河边有滩,沿着河滩可以去到远远的地方。外公每天天还微亮就挑着木工工具箱,拿着一把五尺长的木尺,腰里别着斧头,去到别人家里做木器。临走总要在床上用稀疏胡茬的嘴亲亲我,动作很响的关上门。外公瘦瘦的个子,很高,鹰钩鼻,深陷的眼睛透着精明和狡狯。修长的手指,青筋一根一根,仿佛听得到血液流动的声音。外公的木器箱有三尺见方,外
老家的偏屋墙上挂着父亲在世时用过的几种渔网,静静的,布满了灰尘。一种“撒网”,尼纶线织成,圆锥形,十几米长,近十米的直径,底部有几十个一寸长、小孩手指粗的铅坠连接,站在岸边,撒入水中后成圆形急速下坠,沉到池塘底,来不及逃跑的鱼们只得束手就擒,慢慢收网后,拖到岸边。这种网一般用作网大一点的鱼。一种“起网”,四边形,丈五长,网孔较小,用两根竹竿弯成弧形对角支撑,竹竿交叉处用活结连接一根三丈长竹篙,一端
星期六,老婆回了娘家,我约小玉见面。江边的茶楼很安静,我和小玉面对面的坐着。小玉今天穿了职业装,深色的长裤,白色的短袖衬衫,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了许多。我们话很少,点了两个煲仔饭吃,我把我的菜分了些给她,她把饭给了我一半。她慢慢的吃着,我们的眼睛直直的看着对方傻笑,一片片红霞飞上她的脸颊。进了宾馆房间里,她温柔的靠了过来,我轻轻搂着她。我们吻着相互脱掉了对方的衣服,我抱着她,让她坐在我的腿上,把头
今天接到两个关于生命的电话。老公,我怀孕了。李玮祺,我怀孕了。列位肯定会嘲笑我的数学计算能力太差,明明就是一个电话,你老婆怀孕了。是的,内容是同一个内容——怀孕了,可怀孕的不是同一个人。叫我老公的是小玉,叫我名字的是我老婆。这两个电话可真是让我悲喜交加呀。按顺序也得先说我老婆吧。我们结婚十年了,女儿7岁了,我心里一直都要个儿子,老婆也想给女儿生个伴,可是计划生育抓得紧呀,去年二胎政策下来后,我们加
人近中年,心境自然平静,原来的豪气、潇洒几多不在,每每夜色临至,或抚妻肩,或牵妻手,或孑然一人,在凹凸不平的小区院内,在尾气充斥的马路边,在灯光摇曳或暗黑的金鄂公园,抑或味道颇丰的南湖广场散步,也不辞辛苦地去过汴河街、洞庭湖畔。一般吃过晚饭,手抚圆圆的腹部,摩挲着在小区内走上两圈,嗅着人家厨房里排出的各种味道,这步不散也罢。于是只得跨出院子上马路了。路灯像是一声召唤,齐齐的亮了,暗暗地躲在树叶背后
株洲市往东十几公里,一镇,曰渌口。傍渌水江而名,亦为株洲县城。城虽小,倒也干净利落。因事来渌口镇已逾四月有余,租民房于南岸村。村庄傍山,树荫婆娑。所住之处座北朝南,不甚通风,屋内终日一股霉气,甚于不爽。屋前几棵大樟树高七八长,时时有朽败之叶飘飞,落满车顶,每次开车出去,总于车后撒下一路树叶,确之好笑。工作之余,上街,举目无亲处,只能自乐。逛超市,徜徉琳琅满目货品之中,有时购点生活用品,有时仅仅游荡
记得几岁的时候,我家三间瓦屋里来了好多人,都是男的,个个精神抖擞,大声说话。母亲腾出了两间房给他们打地铺,并把灶台给了他们做饭。我和妹妹兴奋地在他们身边追逐。妈妈告诉我,他们是来修水库的。那时候,我们那里每家每户都住了人,全乡的所有劳力冬天都离开温暖的家来到这个最艰苦的环境中修建一座中型水库。没有机械设备,全部人工,挖平两座山,砌筑两条堤,在山与山之间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水库。想象一下,上万人,
 2025-2050年Solana(SOL)价格走势预测:SOL币未来如何
2025-2050年Solana(SOL)价格走势预测:SOL币未来如何
 媒体人:重大案件减刑挺难,李铁二审刑期得看怎么平衡舆论和司法
媒体人:重大案件减刑挺难,李铁二审刑期得看怎么平衡舆论和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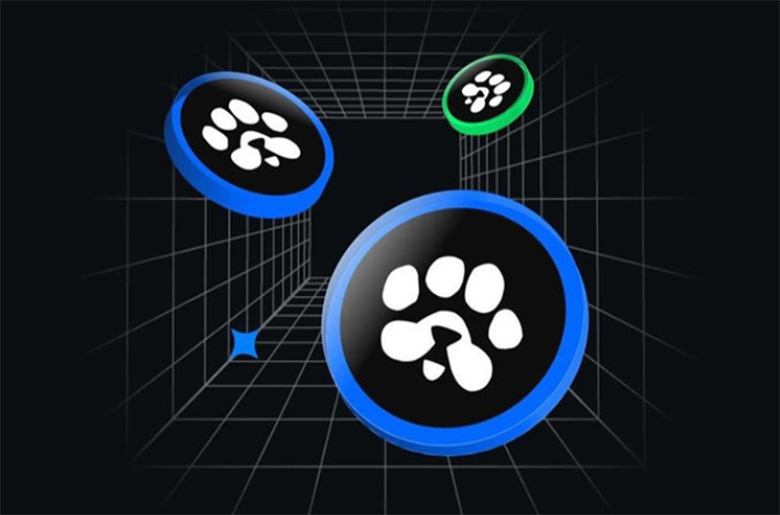 PAWS 空投:如何出售及价格预测(sumswap空投)
PAWS 空投:如何出售及价格预测(sumswap空投)
 李璇谈李铁:相关庭审争议应该在国家队主帅算不算是国家公职人员
李璇谈李铁:相关庭审争议应该在国家队主帅算不算是国家公职人员
 什么是 Paws(PAWS)(什么是质数)
什么是 Paws(PAWS)(什么是质数)
 媒体人:李铁希望证明自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从而申请减刑
媒体人:李铁希望证明自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从而申请减刑
 PAWS 代币价格预测:PAWS 上市价格是多少(platon代币lat预估)
PAWS 代币价格预测:PAWS 上市价格是多少(platon代币lat预估)
 记者谈南基一解约:谈到快两点没谈妥,事关金额+支付时间问题
记者谈南基一解约:谈到快两点没谈妥,事关金额+支付时间问题
 Pi币价格飙升,近期上涨后能否突破1美元(pi币价格?)
Pi币价格飙升,近期上涨后能否突破1美元(pi币价格?)
 意甲主席:如果有争冠附加赛且国米进欧冠决赛 附加赛可能在6月踢
意甲主席:如果有争冠附加赛且国米进欧冠决赛 附加赛可能在6月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