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满的半年一直都是关在房子中度过的。调休,终于可以出去走走,提着包站在路边等车,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将本应该绿草茵茵的春天淹没了,手冷的无处安放。我有大把的时间等车,我有大把的时间站在这里,我有大把的时间感受喜悦的过程。野虎坡那里有个老头子吃力地推着三轮车,冷风里一点点的将他的三轮吃力地向前推移。丢下包,跨过来来往往的车子,没有问是否需要帮助,便将车子推了上来,老头不断地朝着我离开的地方说着感谢的话
1关上原本没必要关的门,将记忆里光着一只脚躺在床上的强子,将冬夜里冷的睡不着爬起来和念辰换着抽一支烟的强子,将掉漆的桌子上的栀子花,将小哎的饭盆子一遍关上了,关上了这个世界上很少被人叫出达家庄的小房子,将两年的记忆一并关上了。很多人都说搬家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什么是自己最宝贵的。念辰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这座一点点地被抛在身后的城市,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一只水杯和一个装着一个馕饼的背包,阿杜用沙哑的声音
说来奇怪,本以为这辈子就跟死鱼一样继续下去,念辰以为此生就这样了,一个人一只狗,一直蹲在世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细数每个晨昏日落。分开后的杜宇有一天将一个很大的包裹寄来,里面全都是用来考试用的书,书的上面安静地放着一张纸条:“辰子,公考的名我们已经替你报好了,山娃说他在林间镇等着你”。念辰点着烟,蹲在地上随手将书本翻动,墨香依旧如多年前一样,甜的很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晚上的KTV依旧人满为患,念辰
家里种着大片的玉米,种着漫山遍野的土豆,这里本应该是一片没有被世俗染指的田园故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看见了城里的高楼大厦,开始有了天价的彩礼,开始将原本自由的婚姻变成了一种捆绑式的交易。家啊,一个人受了伤就想着回去的港湾,杜宇了?每天拉着小自己两岁的弟弟,鞋子跑丢了,晚上回去父亲总会将她压在院子里毒打;每天赶着一群羊出去,晚上又被漫山遍野乱跑的羊溜着回来;弟弟睡着了,她背不动,抱着弟弟将脸
放在桌子上的电话再次响起来,念辰放下手里的盘子,将满是奶油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看见手机亮起的屏幕后,又转身将双手塞进水槽中。三百多条来电未接,全都写着‘粑粑’的备注。念辰离家五年,三年学校,两年的社会生活,他未曾回去,他依旧恨着那些人,恨着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他恨父亲老早对他人生的断言,恨他对山娃喜笑颜开却对自己冷言相加,恨他那句“走的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KTV里的工作依旧那么火爆,形形色
最后一次回到林间镇是在高考结束后长长的假期里,念辰每天都会出去给家里的牛割草,每天也总会将凳子搬出来坐在门口的柳树下,坐在妈妈点燃的艾草的烟雾里,看着他也不知道看了多少年的林间镇的夜空。万籁俱静。成绩出来了,和念辰的性格一样的不温不火,不痛不痒,不偏不倚。坐在树下的念辰被二叔问及将来怎么打算的话。“将来啊,将来就考一个平淡无奇的大学,找一份平淡无奇的工作,娶一个平淡无奇的媳妇,生一个平淡无奇的孩子
?佛说众生分六道:地狱,饿鬼,畜牲,阿修罗,人,天。护身符取各道之形象、种子、真言,置于贴身处,可蒙各尊之加持。????年前好友D新婚,很少主动联系我的他开着婚车穿行两百多公里硬生生地将我接了去。我们坐在车里,他将领带用右手撕开,看着窗外没转头地说:“阿东,给我点支烟”。我们多年不见,多年没有任何的联系。他的父亲早早撒手人寰,母亲将他丢下,转嫁给了南方的煤老板,转嫁给了南方的厨子,后来慢慢退出了所
圈住台历,日子停在了2月14日,情人节多的像日子的填充物。春节姗姗来迟,雪像西洋水彩里的应景一样,节前落下来,北风依旧荡漾在山村的破烂里,亘古不变。在秦安站下车,车上帮忙给一个大叔将行李放到了行李架上,他追着硬要塞给我一支五块的兰州烟。在人海里穿梭,看着忙忙碌碌的人,听着广播里不断重复的声音,阳光从穹顶洒在地上。我知道放假就回家,我知道坐着131就能去火车站,但是我严重的失去方向感,刚子在月台下停
1年三十,所有记忆中最为美好的一天。“念辰”所有人都喊他“粘成”或者直接喊他“520”,这种时下最有效的胶水,念辰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外号,他依旧邋遢地将鼻涕蹭在了早晨母亲刚给他换上的新棉袄上,蹲在门槛上认真啃着猪骨头的二哥用肘子将厚重的门帘掀开,扯着嗓子冲厨房里一片雾气中炒菜的母亲喊“妈,老三又将鼻涕蹭到了新衣服上!”厨房里哧啦哧啦的声音停了下来,母亲将沾满油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跑出来抬起胳膊将念辰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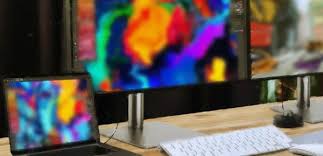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