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初一,五点不到的晨,特别寒冷,坐在副驾位的梅子,面无表情地目送着男人和儿子走进家门。她慢慢地从口袋掏出手机,继而手指急速地在屏幕上滑动着,不一会儿,她从家里扯回儿子,带上两个女儿,冷笑着上了匆匆而到的“滴滴车”。梅子是我的邻居,凤铝铝材店的老板娘,她和男人在县城开店十年余了,生意越做越火,由当初的小加工店发展到现在的凤铝铝材总代了。梅子是个漂亮的女人,身材高挑,穿着打扮也得体。每次看到她的眼睛
清晨,六点不到,星仔旁边的木木从睡梦中醒来,泪眼迷离地问:梦见妈妈走了好远好远,叫了都不理我,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木木的妈妈前一天考驾照时,突然晕倒在地,由救护车急送人民医院。CT片诊断出严重脑溢血,立刻转八楼ICU病房进行开颅手术。木木的爸爸从出差途中折回,痛哭失声。木木今年八岁,是星仔的表弟,跟星仔同读二年级,不同班。昨晚跟着星仔爸爸从医院回来,就在星仔家睡了。这个平时总要被妈妈千呼万唤才肯起
01轮椅上的女人坐在轮椅上,她默默地想:如果早知道当初会有这样的结果,怎么也不会去考那该死的驾照。事实上,她并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不清楚,她怎么样就坐到了轮椅上了。“外婆,妈妈要拉尿。”八岁的木木朝外婆喊。木木是趁着周末的时间,到乡下外婆家来看望妈妈的。木木在县城读书,木木的爸爸在县城经营着以前和妈妈经营的一家店。送木木回乡下后,放下一些水果,人立马就走了。“来啦,来啦,”木木外婆从厨房走出
二爷是谁?二爷当然是爷爷的弟弟了。爷爷老大,就一个弟弟,那就是二爷了。二爷跟爷爷性格完全不同,爷爷严厉苛刻,还会折细柳条打人,二爷却比爷爷和善多了。大老远过来,就先听见他的笑声:嘿嘿,哥哥,嘿嘿…二爷说话之前,一定会先“嘿嘿”笑过来的,你就知道,是二爷过来了,跟爷爷聊天呢。小时候,最喜欢听二爷讲故事了,二爷在哪里讲故事呢?在厅堂饭桌上?在门外树荫下?在后屋大樟树下?都不是。在《怀念堂叔》的文章里我
古稀之年的母亲,还是住乡下,种了一亩多的稻子,还种些菜。有一次,母亲照例带了些菜园的青菜和自家的鸡蛋到县城来。我问母亲:您记得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乡里的口头作文竞赛。作文题目就是写的《妈妈》。母亲笑着说,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那天你们几个在拱桥下玩到天黑才回来。母亲的记忆挺好的,我也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乡里的口头作文竞赛,抽到签轮到第二个上场,题目是“妈妈”,第一个选
堂叔走得如此突然,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无法接受。那天下午,电话铃响:“快!……联系桂子,叫她直接去县医院ICU房……”小弟语无伦次,哽咽失声。桂子是堂叔的大女儿,在县城创业工业园一家工厂上班,公司规定员工上班时间不允许使用手机。直接打不了电话,我赶紧联系写字楼的一个熟人,把十万火急地消息转给桂子:快去县人民医院ICU房!“伤得太重,满脸是血,叫了不应,没用,肯定没用了……。”,ICU房外,桂子嚎啕
酷吏是什么?翻开史书,酷吏是西汉时期严格执行法律的郎官郅都;是制定汉朝多部法律还敢于惩治陈皇后的张汤,是为了升迁大力平定治安而杀害许多小偷小盗的王温舒,是武则天时期利用大批无赖探查秘密,严刑拷打被诬陷官员的来俊臣……说自己的爷爷是酷吏,诚然离谱。毕竟,爷爷出自寻常百姓家,查遍族谱,且不说其本人,就算是爷爷的爷爷,或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八辈子都跟史上的酷吏沾不上一点边。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用“酷吏”
凌晨六点,吃完早餐,送儿子上学。“看,那两个人又在吵架,天天吵架……”刚出门,儿子指着不远处的一男一女说。阳春三月,春分已过,昼渐长,夜渐短,此时天已经大亮了。随着儿子的指向,我清晰地看到,小区转角处的一男一女,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男人个头矮小,一米六几,女人扎一个马尾辫子,看起来反而比男人高些,两人穿着橙黄色的上衣,那是环卫工人工作服。男人手里握着一把扫帚,正在低着头扫着地,女人则拖着一辆双轮保
昨晚淅淅沥沥的雨声,此刻终于消停,凌晨的雨,大概也累极,休息去了吧。五点的闹钟还没响,我却早早地醒了,习惯性地翻起了自己的朋友圈。我被两张美丽的相片吸引住了:一张相片,菜园的藤架,一只青嫩的黄瓜,被绿的叶和黄的花们幸福地簇拥着,漂亮极了,另一张相片,是母亲备的一桌诱人的菜,还有不及桌面高的小侄子,端着碗,站在桌边,仰着头,眼巴巴地盯着满桌的菜,筷子又不够长,母亲弯下腰,在为小侄子夹菜吧。我立刻飞回
有一次,父亲告诉母亲:我数到第293辆时,才看见你下了车。前一年,父亲还能拄着拐,从卧室慢慢地挪到后门,坐着,或倚着门站着。挨着后门的是条一米左右宽的小溪。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溪水是从槎滩陂流下来的,还跟我讲槎滩陂的故事:泰和槎滩陂,是江西最早的水利工程,为南唐金陵监察御使周矩父子凿石所建,距今1067年,至今仍灌溉泰和4万多亩粮田,就近的乡亲都是喝着这口水长大的。挨着小溪的是车来车往的319国道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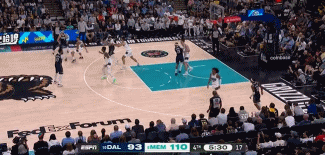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
 任天堂专利并非首创?《幻兽帕鲁》搬出"前辈"硬刚
任天堂专利并非首创?《幻兽帕鲁》搬出"前辈"硬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