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爷爷开口闭口,总说小兆傻,他说他在小兆这年龄段,已谙熟运用“乞丐”一词了。当然,爷爷指的是口语,且仅限于骂人。至于这两个字怎么写,他也不护短,说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小兆今年八岁,马上就要读二年级了。爷爷说他小时候,社会上根本就没乞丐。只所以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和他们是怎么个模样,全是从大人的嘴里听说,日积月累、逐渐成形的。他说他三四岁时就天天跟在姐姐的屁股后面上学,姐姐升四年级,他也想,然老师硬
那时几岁,记不起来了,反正还小,仍穿开档裤。一天傍晚,站在木楼的侧栅窗后,看着慢慢地往山那边坠的太阳出神。西山坡上长满茅草,那花开得正浓,远远望去,整面山坡仿佛铺上一层薄薄的雪,风一吹,那“雪”便浮动起来,像鸭绒、似棉絮,漫山坡飘游飞舞,好看极了。记得那时候在想:山那边是啥地方,怎么个样子,太阳又坠到哪去?这些幼稚的问题数年之后自然有了圆满的答案,只是那漫山坡白茫茫的茅草花自那后就逐年减少,去而不
只所以叫小爷爷,不是因为小方的爷爷个子长得矮、小,也不是他在父辈昆仲子嗣里排末,而是因为小方在向他的小朋友叙述从爷爷那听来爷爷小时候的故事时这样称呼他的。爷爷说他稍懂事,他的母亲——即小方的曾奶便病卧在床,小方的爷爷刚小学毕业那阵,一天他的父亲上山砍柴,又不小心摔伤了腿,柱着拐杖走路还龇牙咧嘴,哼哼咿咿的,不能下地干活挣工分了,实在没办法,小爷爷只好缀学在家,用自己幼小的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经过多
妈妈说那时候我刚吚呀学语,有一天晚饭后,天忽然下起雨来,爸爸正冲凉,妈妈急着要收晾在外面的衣服,于是把我塞给白天不知被电视里哪个没教养的欺惹,刚才又多喝了两口,此时仍坐在饭桌旁生闷气的爷爷。据说我一到爷爷怀里就哭,他只好起身,来回踱着,嘴里这样哼:“小蝌蚪,借尾巴……”然爷爷一曲唱完,我仍不歇嘴。爷爷似乎也觉自己唱得有点不大对劲,于是重新调音定调:“小燕子,丢了尾巴,哭着喊着找妈妈。”这时,妈妈已
吃了棕子,再放几串鞭炮,小慧爷爷那一样自诩水火不侵的金刚不坏之躯就渐渐地不行了,不是这疼就那疼,爸爸和妈妈都快急死了,劝他去医院检查,他说不必了,懒得看医生护士那恐怖狞狰的脸。再者,他晕针。末了,他说:“如果你们真的有那份孝心,就多注意点电视广告,那里所介绍的都是祖传秘方,无病不治,服几贴就药到病除,且有的根本就不用草根树皮、朱砂红汞,只在指定的位置那拿捏几下,病痛就解除了。他还说特别要注意那些档
天天下雨,又闷又烦,傍晚,好不容易云收雾散,还看见西边天际的太阳,天地间一下子宽敞起来。大院里,饭后的小卡和小朋友们玩得正欢,妈妈来了,一拽他的胳膊就走,当然是回家做作业啰,气死人了。小卡的课外作业,妈妈只负责督察,至于过程,她才不管哩,她说放着七七年名在孙山内的文革末期高才生不用,浪费资源。屋里已开灯了,爷爷端坐小卡平时看书做作业的桌旁。今天也怪,不知从哪钻出那么多灰白色蜜蜂也似大、长着薄翅膀的
小花猫离长大,远着哩,也就是说,它眼下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然而,对那把它三兄妹从死亡线上拉过来的看门老头,态度却变了,由爱转恨,有时愤怒到极点,它甚而这样想,等它长大,一定撕破他的脸皮,抓瞎他的眼睛咬破他的喉咙…….小花猫的恨也并非毫无缘由,它听说它那被糟老头送人的妹妹餐餐有肉,大哥更不用说了,隔三差五就有猪肝鱼头,而自己呢,却天天粗茶淡饭,还经常遭那糟老头骂:“滚,都那么大了,还不会到外面觅食,整
人到了一定的岁数,睡眠的时间就减了,像看守南海谢边旧小校园的那个老头,他就说每天晚上睡两三个小时,足够。然老人今天不知咋地破例了,墙上挂钟的时针已指向九点,仍睡得死死的,不知他在做着什么好梦,脸上挂满笑容。这时,床头的手机铃声响了,是居委会治保主任的电话,要他开门,说外面有人找。‘‘到底谁呀,大清早的,还烦劳主任亲自来电。”半睡半醒中的老人心里这样嘀咕着匆匆穿上衣服,拿起钥匙往外走,果见铁栅门外站
哭与笑弃儿不会哭。不是他没那基因传承或变异,更不是他的眼泪早已哭干或泪腺出毛病,而是被他那狠心的爷爷给生吞活剥了。因为不管弃儿怎么哭,即便把的眼哭肿、嗓门哭哑,爷爷总不理不睬,弃儿见哭也白哭干脆不哭了。久而久之,他连怎么哭,方法窍门全忘了。弃儿只会笑,因为他一笑,即便违心,爷爷的脸上即刻出现太阳。为了让爷爷高兴,弃儿就一直强制着压抑自己的生理生性,只笑。弃儿只所以叫弃儿,是因为他来满周岁,母亲便在
第一章二百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中国一个姓毛讳泽东的人曾这样大发感慨说。可惜,毛泽东先生没有两百年的寿命,至于击水,仅三千里吗,不止吧?自负的爷爷“于五行来说,我命属水,然村头那条小河却五次三番想要我的命。至于玩水、我实在不敢和润之兄比了,然这寿数,斗胆说,只要我不和村头那条小泥鳅斗气,离它远点,嘿嘿。“爷爷,听意思您是说您的寿数要比毛爷爷高?当然啰。虎脑希望爷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一刚到爷爷那,小文连个觉也睡不安稳。大门外的广佛路车水马龙。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那时大时小,或断或续、没一点规律可言的轰鸣声,实在让人受不了。然不过那么的几天,小文就适应了。一到晚上九点,那声音就变成婴儿时奶奶嘴里的摇蓝曲。听起来诱人昏昏入睡。二广东这地方,太阳比老家那边勤快,五点挂零,夜幕便悄悄撤去,那树木成荫的老校园内,群鸟都起床了,吱吱喳喳地叫,把邻近那些生物钟早已紊乱,且住所隔音并不太好的
一小仨转学到妈妈谋生那地方就读的那所学校,“寺庙”虽小,然供奉的菩萨可大着哩,就班上那几个平时和自己玩得来的同学,傻乎乎的连抹鼻涕口水的姿式动作都不标准规范,然前几天他们聚在一起闲聊,有的说曾随大人飞到万米高空,亲眼见证我们所居住的大地是曲面,有的说自己已隐隐琢磨出三维以上空间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有的说自进入二十一世纪,有人对爱因斯坦的两论提出异议乃至质疑,有的说……听了他们那些并非故意炫耀显摆的
木头人——不用猜,能称得上这尊号那主肯定极其呆笨愚傻,木纳迟钝。木头孙的爷爷就是附近十里八乡公推获此殊荣的人,他这一辈子已被强行更换了三次名号,儿时叫木头崽,长大后称木头人,上了岁数,又改成现在的木头翁,至于他百年后的遵谥,据说人们也早拟好腹稿,就等那一天了。而木头孙只所以叫木头孙,那是因为他本就姓孙,又是木头翁的亲孙儿,这雅号自然当之无愧,托爷爷的福,沾爷爷的光了。知根知底且颇为公正的舆论是这样
一在爷爷的房间里,一个和简陋的台几搭配得并不怎么和谐的笔筒里插着一撮鸡翎毛,那笔筒可有来头了,南海谢边小学迁新校时,校长随手送给他的。妈妈说那撮鸡领毛的年头比我的岁数还大哩,乡下人养鸡,早上从不喂的,打开笼门任其四处觅食,傍晚才拿出几把米,嘴里发出“咕咕”声,把它们召集在一起,随手往地上一撒,再不管了,说实在,要不是为诱其回笼、那可怜的几把米有没有还说不定呢,故老家那里,要把一只鸡养大,没八九个月
一篮红薯大困难时期,我已六七岁了,按理说像我那年龄段的孩子头脑里也该装点事了,然在我的记忆里,除一篮红薯,别的一片空白。那篮红薯大慨有六七斤重,哥哥带着我放午学后顺便到队里的食堂领的,是全家人一天的口粮,至于当时我饿不饿、馋不馋,没印象了,只记得我和哥哥轮着提那一篮红薯回家,路上我没闹着要吃,哥哥也没起那头。那时全家五口,妈妈、奶奶、大姐、哥哥和我,而大姐已到外地读书,那篮红薯没她的份。这也许是我
孝道三篇一、钮爷挣工分吃饭那时代,钮爷的母亲已上了年纪,失灵了。孩子们干活去,听到栏下猪叫,便把锅里留下顿的猪食全舀光,你以为他舀到猪食槽里呀,不,全舀到地板上和屎尿混在一起浪费掉,一面舀嘴里还一面这样说:“哼,这种孩子,猪食煮了也不喂,就出工了,看它们饿的,叫得心烦。”那时候,我们老家那的房屋清一色都是木楼式结构,上住人,下养畜,为方便,煮猪食的锅灶就安在猪栏旁。就这样的一而再,钮爷只好每天早晚
蒙冤今天是望日,天又特别的晴朗,或许是太阳、地球、月亮一家三代马上就要在这样难得的好天气里聚在一起叙亲情、拉家常那原故吧,整个下午,懵懂爷的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傍晚,他特地炒了几个好菜,把桌子搬到操场中央,再差小汪到大门口旁边的小卖部,让那个瘸腿店主老头送两瓶糊涂酒过来,把多余的几副碗筷全摆上,等月亮探头,方启塞开盖,邀过日月山川,八方神祇后,才自斟自饮起来。小汪其实是一条狗,还小,两个月前,它
联语三副一去年腊底,在友人处作客,见其案头有承基兄所著的《鉴水留芳》一书,乞借,回寓所后一口气读完,颇多感慨。漂泊流浪了大半辈子,一向怕敢在人前提更怕别人问起的故乡德保,熟料在历代文人墨客眼里竟如此的神奇曼妙,多彩多姿,还养育出那么多的英杰才俊,也不知承基兄磨破了多少双鞋,走访了多少耄耋老宿。花费了多少心血才写下这本书,使故乡的奇山异水得于展诸于世,让那些英雄贤豪的名姓事迹得以流芳千古,兄功也。把
托福年少不更事时,受鼓惑,如醉如痴地迷上了苍喆、毕升两祖宗的“活字堆垒组合”之第十一阶幻方这一千古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好多年后,还真的给我窥出点门道来,于是更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泡上,别的啥也不管不顾。一天,父亲雇了艘船,带我出海游玩,午后,留连忘返的我被一直站在身后的母亲一脚踹下船头,那船也随之转舵,扬长而去。海水又苦又涩,好在呛下后喉头有丝甜味,可惜那水浮力极差,精神略放松,四肢稍怠懈,
儿时的梦一戆子的家乡,地处祖国的大西南边陲,养育他长大成人的那个村子,名叫大屯。名副其实,大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五十来户人家,人口近三百,十里八乡名列第一。屯大人多也有屯大人多的好处,五零年土匪暴乱,小的村屯多被洗劫,村村自危,而大屯却绝无此忧。当然、大屯的人也不仗着自己屯大人多而放松警惕,青年民兵一到晚上便轮班站岗。巡逻放哨,他们有的还是游击队员,持真家伙,而手里只有鸟枪火铳的土匪想打他们的主意
 直接点赞!rita晒双城之战主题卫衣照片 黑白穿搭更显清纯
直接点赞!rita晒双城之战主题卫衣照片 黑白穿搭更显清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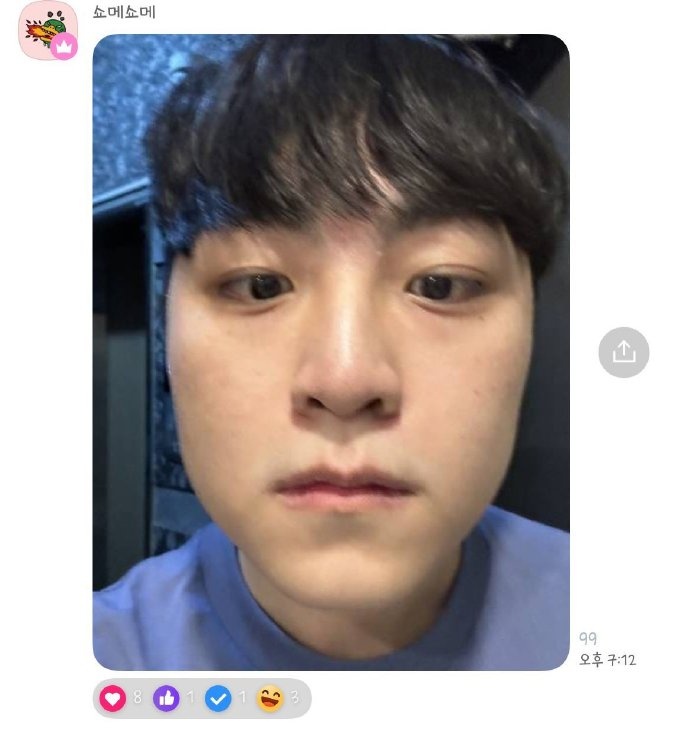 直男自拍?ShowMaker社交软件上分享直拍大头照
直男自拍?ShowMaker社交软件上分享直拍大头照
 转行卖衣服了?无状态更新微博晒穿搭:主要是好天气
转行卖衣服了?无状态更新微博晒穿搭:主要是好天气
 有点糙?网友发现:Zeus宣传片里举的HLE旗子上ID还是Doran
有点糙?网友发现:Zeus宣传片里举的HLE旗子上ID还是Doran
 大家想看的不是这个!iG官方:下路Ahn正式离队
大家想看的不是这个!iG官方:下路Ahn正式离队
 RNG欠薪让Ahn失业?爆料人调侃Ahn找队:蝴蝶效应 造化弄人
RNG欠薪让Ahn失业?爆料人调侃Ahn找队:蝴蝶效应 造化弄人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呀!Leyan前女友晒照:低胸背心 天赋尽显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呀!Leyan前女友晒照:低胸背心 天赋尽显
 新阵容呢?iG官宣:辅助Vampire成为自由人,即日起正式断开连接
新阵容呢?iG官宣:辅助Vampire成为自由人,即日起正式断开连接
 《黑神话》获PS合作伙伴大奖,冯骥获奖感言:这一切都要多亏《西游记》
《黑神话》获PS合作伙伴大奖,冯骥获奖感言:这一切都要多亏《西游记》
 善良啊!吴柳芳回应直播间关打赏:受之有愧 不是努力得来的
善良啊!吴柳芳回应直播间关打赏:受之有愧 不是努力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