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许是快到了,但风却仍寒冷。立春虽然已久,却不见有春的气息,冬天大约是没有远去吧。我看着窗外木乃伊般的老树,轻轻地叹了口气,道:“这冬天,许是要留存很久了。”周先生看了看我,扫了一眼鱼缸中缓缓游着的金鱼,道:“今年的冬天有些长,太长了。”九一八事变,到今年已经有五年了罢。我这样想着,挨了一阵寒风,打了个寒战。“去外面走走吗?”周先生搓了搓手,提议道。我点了点头,围上了围巾,这天太冷了!我和周先生
那年夏天,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江堤下。夕阳已落,淡粉色的帷幕渐薄,黛色爬满了天空,只有天际有些许青色的霞还赖着不走。骑得倦了,就躺倒在防汛林里。月上树梢,被枝桠撕碎。美,是的,但是并不凄凉。风过枝头,拨动木叶如轻抚琴弦。月,看起来是那么壮丽。破碎着,闪着皓白的辉光的月,照在我的脸上,照进我的心里。本自有盈缺,何妨观残月?借着骑车想要宣泄的那些不快,那些闲愁,在月光里显得是那么渺小。我想起了春江里的那
那是,我大概是六七岁吧。但是季节,月份之类的细节甚至是来的原因都早已忘却,只记得那是一个晴夜。墨一样的天空中,高悬着一轮杏黄色的明月。就像文森特。梵高孩子一般地感叹金星的璀璨,只是个孩子的我,发出了惊叹“好大,好亮的一轮月!”但月并不完美,杏黄色的镜面上,似是有些他物。我想起了奶奶说起的故事,那是她的奶奶曾说给她听的:月亮上有清冷的宫殿,里面住着嫦娥还有一只玉兔。也正是这个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
为什么,记忆中是这样?为什么,“月”是这样?书上的字,虽是不经意的一瞥,却让我思绪万千。甲骨文的“月”,只是个拙朴的半圆,但是到了金文,“月”的半圆中,却多了一点。那个点,究竟蕴含着多少的意味,浸润着多少的思绪,承载着多少的记忆?这是关于月的疑问,更是关于记忆的疑问。记忆的答案,亦只能从记忆中探寻。
有没有某一天,在书架前浏览,突然被某一本书吸引,粗略一翻,心中便已经垂青。考虑到书的摆放,他人的借阅,自己无目的的浏览,这实在是小小的,但确实存在的,奇迹。就像独坐栈桥,遥见海豚自水面跃起,就像俯首案前,忽逢月光透云帷入室。古人书之为天命,臆之为神谕,但在口耳相传中,它叫,相遇。第一次,从一本阅读练习里遇到了《杏黄月》,同样的文字,当时所见,仅是华藻流岚。就像在人群中擦肩而过,却未曾有半句言语。遇
当老佐背着渔具走到小区侧门时,突然响起的防空警报惊得他打了个激灵。他下意识地望了望天空,没有一朵儿云,连风都是轻轻的,路边的树叶垂着,没有一点声音。老佐收回了目光,想起今天好像是个什么日子,便紧了紧背带,继续走着,只是这渔具似乎凭空重了许多,好像一把枪。自疫情以来,老佐已经很久没钓过鱼了,把式生疏了许多。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手痒,时间久了,却是碰也懒得碰了。如今局势似乎缓和了许多,钓友们极力邀约,这
 下一个暴涨的虚拟货币预测:哪些币种有潜力?
下一个暴涨的虚拟货币预测:哪些币种有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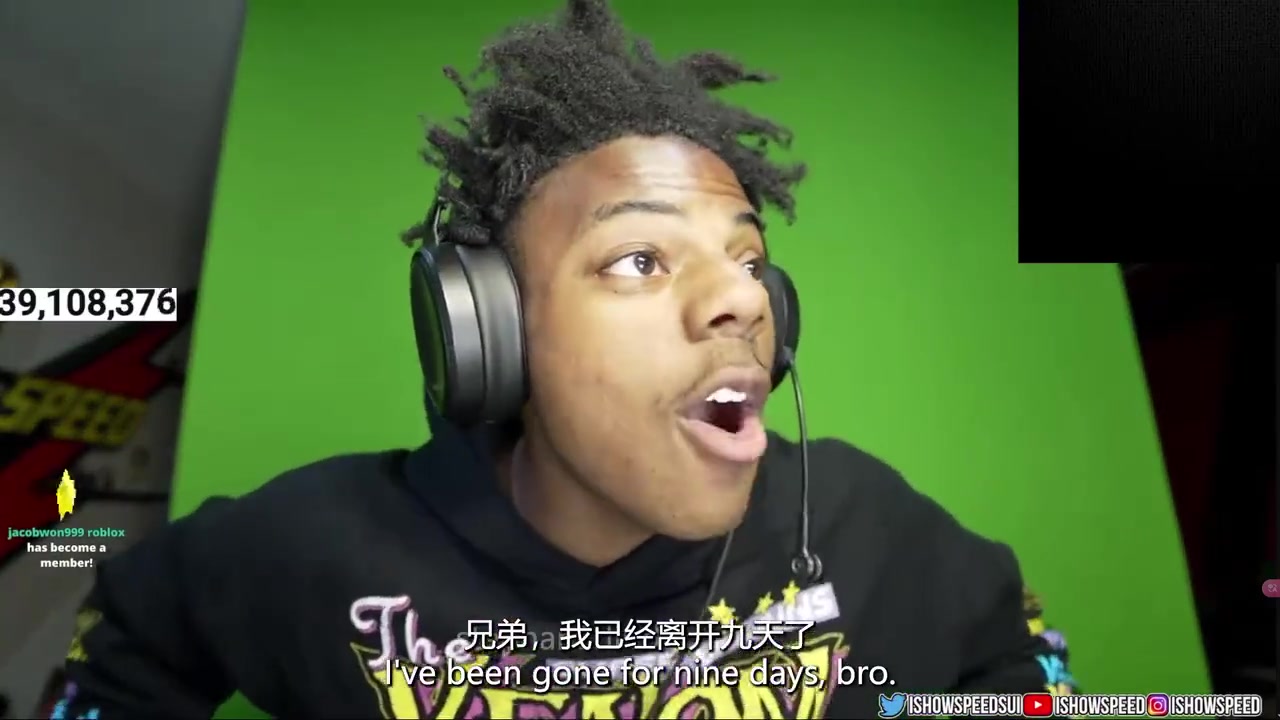 甲亢哥回国后首次直播,给中国打9分,并表示卤鹅大叔几周后会去美国
甲亢哥回国后首次直播,给中国打9分,并表示卤鹅大叔几周后会去美国
 4月22日辽宁铁人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 锐意为锋,勇者无畏
4月22日辽宁铁人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 锐意为锋,勇者无畏
 普通人如何投资区块链?2025年国内区块链布局分析
普通人如何投资区块链?2025年国内区块链布局分析
 徐正源赛后:力克海港展现蓉城DNA,成功弥补主场平玉昆的遗憾
徐正源赛后:力克海港展现蓉城DNA,成功弥补主场平玉昆的遗憾
 他在练了!TheShy:快速适应不同版本是一个上单最重要的能力
他在练了!TheShy:快速适应不同版本是一个上单最重要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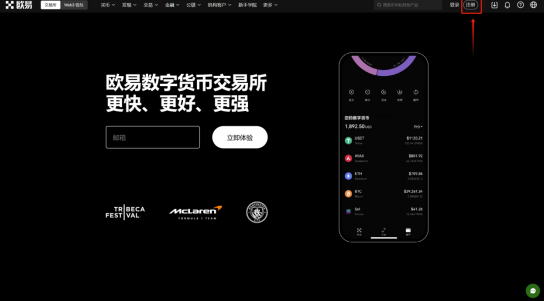 手上有几十个比特币能干嘛?有10个比特币可以一次卖掉吗?
手上有几十个比特币能干嘛?有10个比特币可以一次卖掉吗?
 东体:泰山近两年踢强队总是输,1-6惨败显然不只是红牌可以解释
东体:泰山近两年踢强队总是输,1-6惨败显然不只是红牌可以解释
 JDG赛后群访 cvMax教练:对手整体BP做的不错 第三把整体上有失误
JDG赛后群访 cvMax教练:对手整体BP做的不错 第三把整体上有失误
 THE币价格能涨多少?THE未来价格预测
THE币价格能涨多少?THE未来价格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