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的月光属于麦垛里的蛐蛐儿。那时的麦收一律手工,要经过割麦、拉麦、晒麦、铺场、翻场、收场、轧场、起场、扬场等许多程序,才能把籽粒收仓入库。因此,一个麦收期,往往要过半个月,二十天,甚至更长时间,这期间小麦要放在村外的场院里,需人看守,以防火、防盗和防牛羊来吃。于是,晚上就成了我们这些守麦场的孩子们
家里喂着牲口的时候,要给牲口供应足够的青草料,拔草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儿。跟我年龄相仿的小孩子中,绝大多数对做农活儿的启蒙,是从拔草开始的,勤快的人都是夏天早上五点就出发,七点回家吃早饭,然后上学;下午六点放学后就立即背上编筐(或编织袋)出发,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五岁那年的夏天,我用自己的双手拥
奶奶的去世与爷爷相差一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很冷,母亲坐在车辕上赶着驴车,车上用一道麻绳拢着垛的高高的棉秸秆,棉秸秆上坐着奶奶,奶奶怀里揽着我,我怀里则是小我两岁的弟弟。驴车晃晃悠悠的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左右颠簸着,不时让奶奶和我发出心惊胆颤的叫声,我紧紧的抓住身边的拢绳,生怕车子歪到一边回不来。意外突
人在苦闷无奈之时,会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由远而近,由模糊而清晰,就像着了魔一样无力摆脱。很多人经常讲述童年的美好,事实也许并非如此,过去的生活不会永远的充满趣味,在那许多的场景、许多的人物、许多的表情、许多的心绪中,有快乐,也必然会有沮丧。记忆是一张阴阳脸,有黑有白,有美有丑,有肮脏有洁净,所以才
北风比暴雪刚强的理由,存在于北风烈酒般的自由意志,而暴雪只是个粗人。毫无畏怯,向着自己坚信的真理奔突,绕过所有城堡的困堵,从未想过在将来的某一地,粉身碎骨会成为可能。冰花低垂,街道冷清。希望格外的明朗,就在暖阳下残雪的泥土中。冷漠与热情在各自的天地驰骋,碰撞,顽强,悲壮。你做全世界的英雄,我做我自己
爱可以让人变得迥然于己身以往风格的包容。人生也许不是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另一半,也不是在寻找自己最爱的人,而是既已走在一起,就很难再放手。用日子轧出来的感情和一见钟情中的情份根本不同,后者可以决断放弃,前者却不能,那种难以割舍可以让一个坚强的男人放声大哭。正因为如此,许多伤痕累累的心虽然已无力承受更多
海子很善良,海子是个男人,海子却只爱男人。在一个夏天,海子满不在乎的把他的故事告诉了我,我没有诧异,没有同情,没有感动,没有躲避。我以为他真的不在乎,我说:“现在我理解了同性恋!”没想到他马上翻脸似的说:“理解什么!这有什么好理解的!”说完,扭过头去,然后又略带发怒的歉意说:“其实没什么,挺正常的。
比悲哀更悲哀的是望秋远去。急匆匆,漫无目的的前行,将夏日的凉爽,冷冷的甩在身后,灰尘会在脸上积成一层土,将疲惫渗透着,直到血液,忽略了皮肤。隔着玻璃,能看见醉了的人将酒倒在嘴角,带着咸味湿了衣裳――隐藏了深邃到心的迷茫,叫人记起,牵强的笑容从来无力掩饰真正的落魄。几片落叶在秋风中飞舞着,飘荡到一个狭
晦雨连天的时候,让人忆起秋天的男人。喧闹之后,静默到冷。那种冷意可以穿透衣装,直浸肌骨,最后到达那些曾经热情和奋斗着的心灵,汇成一丝凄凉,微微颤动。生活是忙碌的,是嘈杂的寂寥。花都谢了,叶都落了,根呢?触目皆是在风中抱紧自己身体的生命,陌陌一望,然后低头,揪出自己的心事。公交车也跑的落寞,互不相识,
无论是奔波忙碌的普通百姓,还是街头游荡的流氓混混,谁不曾有过厮守终生的爱情美梦?无论多遥远,毕竟曾存在。我们能相信几次这种看不见阳光的未来?怀着厮守终生的梦,去开始一段全心全意的旅程――付出,执着,最后梦醒了。路并没有错,清醒只是缘于邀约之后的疲惫。她是另一半还是另一个?最后她竟成为陌路人中的一个,
人总该爱上一个人,方显社会属性的充实。人们都说,这个世界若是没有爱,便与荒凉的沙漠无异,其实潜指的多半是爱别人,而被爱则是其后,甚至置于次位。爱和亲情如同性和吃饭一样,都是人的本能,一个实在没人能去爱的人,便会转向爱自己。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找不到可以有结果的爱的对象,也必然有一个不可能有结果的
之所以有人爱憎分明,是因为脆弱和坚强往往是一个共生体。爱所有给予自己的人,恨所有伤害自己的人――情感愈是强烈,爱与恨的矛盾便愈炽热的交织在内心的深处――有些人,总是给予你很多,又伤害你很多。爱要爱的深沉,恨要恨的彻底――与其说是一种坚持,不如说是一种保护――本能的保护自己内心的一切。有些苦,有些累,
最纯最真的爱情,是孩子的爱情。那是被所有“已经长大”的人所漠视的最具震憾力的爱情――没有贪欲,不计财帛,未讲任何条件,纯的让人流泪。他们是否懂爱?在上帝面前,所有人类的灵魂都是平等的,甚至,孩子比大人还完整。年少时的爱是幽谷里的爱,一丝虚幻,一缕忧愁,天地之间,只有情是真的。不去沉思和严肃,就已是一
我对希望的感觉很特别,那种冥想如同大雁在幽深的箫声里孤鸣,虽然未知前方的快乐究竟有多远,心灵却执着的飘浮寻觅。夏日故乡的白杨便挂满了这种影像,高耸挺拔着,夹盖了整个柏油路,透下的斑驳阳光花了眼睛,整个天空都变成了迷离的幻想。头上是白杨树,身边是白杨树,路的尽头是白杨树,他们全然不顾曝晒的阳光,轻轻摇
如果你认为孩子只有孩子的想法,那你就错了。每个人的狼狈都只是一时,而幸运则是永恒,只看你对成功怎么解释,而他,则宁愿把“感冒康复”也称作成功之一种。乖孩子有人喜欢总有他的道理,他们相信大多数的书本,他们从不直接对前辈的教导不屑一顾,因此,他们收获了成长和那些最真的、普遍的、极易被人忽略的真理,如:坚
整个小学期间,我都是孤独的。那时候,在大多数人眼里,宗教只是一个迟早被消灭的愚昧的代名词罢了,圣诞节只是地球另一面的遥远传说而已,而像念经、告解、圣体,更是说不出的怪诞与荒谬。“哎,咱班上有一个信天主教的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当一群山羊当中只有一只小绵羊时,这只小绵羊该有多扎眼!?“听说他们还念
经历了太多父母甚于深仇的撕打谩骂,让我长大后对爱情具有本能的苛刻要求,只有我自己知道问题的根结所在,但既已成为人初脑海中的印迹之一,奈何无力真正忘却。那时候我只是个三四岁的孩子,无数次觉得世界已经末日来临,睁大两只极度恐惧的眼睛,蜷缩在墙壁的角落里,抽噎,颤抖。一次又一次在睡梦中惊醒,黄豆似的灯光下
这是一个偏僻的村庄,却属于本地区的中心。教堂和楼群是近百年前德国人建造的,青砖碧瓦,宏伟庄严,纯粹的欧式古典建筑,高耸的塔顶钟楼里的大钟,声音能传方圆几十里。逢大瞻礼日,全县堂口的教友到这里,谁都远不多少,谁也近不多少。我姥姥家就在这个村子,那些年的寒暑假我都在这里过,只因为这里有我感兴趣的突兀的建
按照天主教的传统,我在出生后不久即领受洗礼,洗名为方济各。七岁那年,我开始在神父的指导下诵读《圣经》,并在次年“开神工”,办了告解圣事,而且在神父那里领取了一张圣方济各图片作为纪念。因为教会刚刚复兴,神父做弥撒缺少助手,我也开始学习辅祭,在神父送圣体时帮拿托盘,或在弥撒过程中摇铃,这个工作没坚持下来
在我四岁时候发生的那场灾祸中,当我被人从冰冷的河水里捞出来,瑟瑟发抖的回到自家的炕上,睁开第一眼所说的话是:“文奶奶在哪里?”我所难得的那些慈爱的温暖,大部分来自文奶奶。文奶奶是个寡妇,丈夫早就死了,没有儿女。文奶奶三间破旧的土房,是我小时候放学后的第一站,房里高架在门框上的玉米面饼,是我饥饿时候最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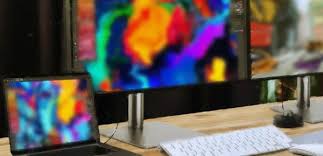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