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是一座烟雨古城。大概因为烟雨,春风走到这里,脚步就有些不忍。多好的景啊,毗连成片的青砖小屋,夹着一河散不去的氤氲。两岸垂柳低着头,晨曦中自顾梳洗,那般娴静。那份神态好像说:才不怕人偷看呢。看吧,看吧,让你看个够。更有几座小桥,将两岸人家挽到一起,好像出门的孩子,一手拉着爸爸,一手牵着妈妈。无论桥
“阿姨,点一首歌吧,点一首歌吧!”声音细若游丝,如果不是抬头与凑到跟前的小姑娘的目光相遇,在这个人声嘈杂的大排档里,这种音量很快就会被吆喝声、锅盆瓢碗的撞击声淹没。“歌童!”一个从“花童”演绎而来的名字那么自然地出现在脑海里。记者细细打量眼前这个肩上斜背一把吉他的小女孩,十二三岁的样子,一张稚气未脱
一写下这两个字时,我的心中一阵悸动。这两个字于我已很遥远,又分明每时每刻都在我心里。母亲早已离我而去,去了遥远的天国。这些年,我写过无数篇文章,却没有一次提及我的母亲。因为我怕我粗糙的文笔写不尽对母亲的爱,亵渎了母爱的神圣。我的母亲生于胶东半岛一个普通家庭里。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兄弟几个全是十
今天遇见大哥了,他满脸的憔悴,眼里有血丝。他是太累了,企业又扩大规模,增加了出口项目。不累才怪。大哥不是我的亲大哥,是一个大哥式的朋友,认识他的人都这样叫他,我也这样随着叫了。我认识他大概在七年前吧,一个偶然的事故,他一下子失去了两位亲人。而责任在对方,按常人的推理,既便他不去闹,对方也脱不了法律责
一直觉得我姐的一生是个悲剧。我姐要出嫁那年,我才十四岁。姐要嫁到离家五十公里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个是我姐夫的人在等着娶她。关于我姐谈恋爱的过程在我记忆里全省略了,只记得突然有一天母亲说你姐要嫁人了,就嫁了。是一辆军用吉普车把我姐拉走的。那个时候在农村坐车出嫁的真说的上是很体面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
姐姐在电话中说,老家院子里的月季花又开了,开的红红火火。那些月季花是我离家那年父亲栽的,父亲知道我喜欢花。在家的时候,每年春天,我都在小院子有限的空间里划划锄锄,栽一些女孩子喜欢的花花草草。但我从没栽过月季,总觉得月季的花色太艳丽,艳丽的有些俗气;花朵太丰满,丰满得缺少含蓄。而父亲却说,月季的花期长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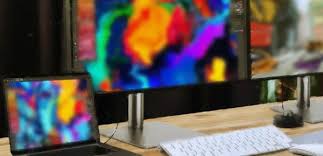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