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声一把素色的伞雨落石阶声鞋跟声还有白生生的握伞的手背上那淡青色的几条若隐若现的血脉柔柔的缠着我的呼与息
如果天上没有银河如果相思没有相隔七月再也找不到那一天如果天上没有虹桥如果相思没有相见七月再也找不到那一天
乌云镇的云,在落日中晶莹剔透,如梳妆的女子久久端详着自己的样子,不时的变化着总是不如意的身姿,映在江底,如鱼儿般,婀娜的飘。落日在江对岸,悠远绵长的俄罗斯的山峦上,着了魔力似的散发着眩目的余辉。闭着眼,仰起头,沐浴着这夏日江边的灼热。脸上突然有了一种轻微的,痒痒的碰撞,如她略过的唇,拂过的发。不想睁
她在教室后排的计算机旁,找到忙得正脚打后胸勺的我。“吃饭,吃饭,先吃饭。”不由分说的被拽起,洗手时,看着她秀气的脸,听着细声细语的累与不累的问候,忍不住问,“也是温州人?”“不,齐市的,”她花枝般笑着摆着手。她和她爱人是中间商,到学校催款,随便来看我。难得的是能在这最北方也能看到中原遍地的温商,而作
父亲走了,魁梧,壮实的他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每当经过那家医院,便如经过一片阴影,压得喘不上气来,总想躲过它,却总是不由自主的经过它。父亲是广州人,年轻时就来到了北方,朴实,帅气的他认识了刚刚当上教师的母亲。七岁以前的记忆是在乡下。母亲下放,四个孩子和父亲也都跟去了。村口那高高的如屏风的台墙和那在奔
象片向日葵,头都朝着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不同的是,那个方向没有太阳,只有车来车往的永远不是你所等的那辆公交。祈祷的,咒骂的,麻木的。都在一眨不眨的盯着,仿佛看到了,就坐上了。但谁都知道:车来,只是战争的开始。最近去化工大学维修,不得已的卷入这场晨战,路上,车如万兽奔腾,路旁,等车者如猎犬般守候。望穿
麻木的骑着车,感觉路上象少点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了十字路口,被擦肩风驰而过的车一路训斥着。才意识到路口少了吹哨,举旗的。多年的交通协勤,已习惯了不看路灯,只看举旗的了。日头像相思时的她,怎么也躲不开。路那边的地铁口,透着森森凉气,张着黑不见底的嘴,嘿嘿的瞅着他笑着。落寞的停了车,上了锁。不是上
等车的地方,有棵树,树身有一处伤痕,伤痕如阿凡达般,让过者路过后,总是回头。树不高,两米左右,不粗,单臂可揽,有三只粗干,弯弯曲曲的指着冬日里浮白的天,树身的一半处,已枯掉了两尺左右长的树干,伤处深至树干的三分之二,风过时,总能听见那薄薄的另一半,发出吱吱的声,不敢眨眼,怕它转瞬就折了。树身的伤痕如
九江的田园在冬季也如手中的绿茶一样的温和,铁轨两侧的麦香一路追随着列车,遍野的桔黄诱惑着一路疲惫欲睡的眼。景德镇中学的语音室,老化严重,维修很费劲,在教室里闭关三天才算修好。校长派了一位英语老师一直跟着我,忙这忙那的,很年轻,刚师范毕业,说话时总是不敢正视我这北方来的人,总是站在我的身后,在我站起转
大雨,单车,风中摇摆的伞。圣代,空椅,灯下婀娜的影。秋雨,在伞外,如盛极的花,淋在脸上,身上,瞬间的开,瞬间的谢,每瓣都映着她等他时的影。单车,一路碾碎着水样的花瓣,手中的伞在满天的秋雨中摇摆,被如珠的雨滴敲打,如天籁般久久的传着她等他时的心跳。冰冷的圣代,纤细的手指,透明的勺。薄薄的,一层层的刮,
如果声音可以相恋。窗那边的夜,一念间,已探进窗这边。寻不着月,寻不着星,寻不着方向,如深深的深海,心念陷在里面,越拽越深。她说,她想听,他的声音。手伸向漆黑,摸到了手机,屏上的莹光,惊走了夜。铃声轻扬,在耳里跳动。铃起,铃落,再起,再落。能感到她的指在接听键上的起和落。铃止,静了几秒,“喂,”声很轻
懒懒的,把车停在一旁。躲着躲不开的炽热。阳光象燃着的沙,在头顶倾泻,从心事一直掩到眼所见着的。径直的走向那,看看时间还早,就将眼落在身后那面橱窗上,静静的等着被炽热凝结不动的时间。窗内显着深深浅浅,斑斑斓斓的色,如黑白电影般掠着窗外的世俗,在深深的深处,有一青色的若瓷的物,藏在那,不仔细,看不着,风
昏沉中,感觉她在售票的女子急匆匆的牵引下硬塞进已很窄的座位里,黑色的羽绒服薄的能触到她纤细的臂,正在尽力的向内收,怯怯的,与他这陌生的男子保持着一指的距离。白晰的手,透明的指甲,藏在黑色的,单薄紧闭的双腿里,随着车的颠波,如窗外黑黑的夜里,枯黄的麦尖上,莹莹的一丁一闪的雪。晚上赶路,白天维修,三天没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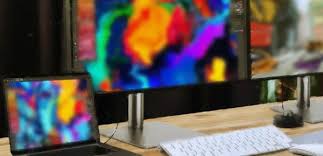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