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魄李尔王,秋山苏东坡 傍晚之际,外面的市声应该略微,妻子问要不要出去走走,我说宅在家里吧,你自己广场上散步吧。我心依静,再见旧朋邻友,恐怕聚众喝酒,泛滥流言。已经两天了,关掉手机,或看书笔记
用一百年来恢复 昨天我已经恢复了正常,或者说昨天已经不再多饮酒,但需在补录笔记的时候,从前两天晚上记起。那天四点多些,结伴值班的同事打来电话:今晚你准备菜,我准备酒,有两位局领导、两位老同志,
卧榻之前的节令雾霾重重,一个节令的上午,街上少人,市声稀零,没有起床健身锻炼的意愿,而是卧榻读书。一读寓言故事,巧遇了《童区寄传》,柳宗元先生的记录。用剑刃锯绳,绳断束缚捆扎,而宰一贼人;又巧言制计,瞒哄余贼,火烤素绳,又杀贼。哎,只不过一个11岁的少年,所谓比燕国当年的刺客秦武阳还要小两岁的少年。如此不禁自惭,想想儿子已经16周岁,那些英雄少年,不同的时代吧,英雄的红军不都是十五六岁吗?时代不同
如此安逸的现世他是安逸的吗?无人打扰,可以有只鸡蛋,一点儿咸菜一盒儿牛奶,三两的薄酒,边就食饮酒,边看电视,甚至写一张字,有案可俯,然后看一眼窗外的黑夜,还有门外寂静的走廊,银色灯光圆满一半空域的走廊,便可选择电视频道,历史或传说或故事,笑谈也行,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点染中、声音中沉沉入睡。直到不知道其何所在,竟然梦到了开会,不是在我们的机关或下面的学校,而是去别处的地方开会;或者被深深的隐然长久
开窗的玉石阳台上的花草,自栽培的蒜苗最为旺盛,妻子曾经端详过不止一次她的念想,其始其间其次,那蒜苗碧玉一般,不,墨玉一样沉静而晶莹;和妻子共同是两株美好的生命,也就此是他们之间的相互照应,回到最美好的时空,展现魅的一面,在我的家居和我的记忆之中。回到卧室的沉静和温馨,想起昨晚朋友的交谈,当说到“他年人渡我,此时此际人自渡”时,我们知道,沉静、自执和自悟的那些认知和情怀,已经笼罩着我们,那浓浓的氛围
曹旭烽火戏诸侯“你那一次喊来我,喊来去,乖乖,十来门,都去了!”他给曹旭说的时候,外面寒风凛冽;据说北京阴霾连天,正传降温和雪降的消息。屋内酒桌,牛肉一道,一道白菜豆腐,分别半斤烈酒。正说的欢:“怪不到朋友喊你半仙儿,你真神经啊,都去了,乖乖,都去了,可是你哩,你招呼好朋友,一会儿,趴在酒桌上醉了。兄弟们接到你醉之前的电话,相继过来了十几个,以为是什么事儿,想着怎么了,原来是喝酒,喝酒就喝呗,一会
任你飘摇我自镇静早晨从北面过来,渡水而来,围着喷泉的暗红色弧形跑道跑步或疾走高呼的人,“哈!------哈!”一个长调,于是东天欲晓,晨练的人陆续在广场的高台、园场、花坛之间影影绰绰的活动着,南面我肩膀不远的大道,车辆流动起来了,我脚下的不宽阔的河水,在人言车声之中,划过一个弯线,无音流向南方。我睡着了,模糊中,我的静从西面缓缓而来,伴着黄昏的瑰丽色彩,从可知的远山和近处的高厦缓缓落下,伴着老者的
最末的一天读历史用泪花说那缓流的河水,墨色的雨是那初秋的草原,还有江河失色,群山蒙面,风挥不去,雪掩不失,来形容这个民族,足可以形为遗迹,相得益彰。这个民族是屠城无数,杀人流河,征伐百年万里的上帝之鞭,蒙古铁骑。所谓情景交融,在历史读物中,依可通用,也是内在的规律。作者是一位老师了,当然,较之华丽辞藻和全貌概述,历史的真像,那些细节的真像亦可入笔,说“十月十号,你家的菜刀该我管了;你吧,从明天开始
最好的家庭是街坊来不及看橱窗后面的故事,那些《晨报》刊登的“最美”、“凡人好事”、“道德模范”,那一张张图片,图片上的人物,那一张张或沉静或微笑的脸色。但这有假吗?这些凡人所做的非凡之事!真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吗?所以听到一位面相怪异的老人,路过我们的志愿服务台时,故意嘟囔说:创文明城,创文明城,创上也是假的!我不由得看了他一眼,又追上他的背影,看他与同伴在十字路口张望,身体歪斜着,等待着什么。哦!
在桥与桥之间往来一旦了解,便了无趣味,原来的和尚桥的传说,不过如此而已,就是明清之际、很久之前的一人,寡母与河对岸的一个和尚私通,此人怜母,也有怜和尚的份吧,修浮桥任其通行。此人后来成才,便孝敬母亲至终老之后,杀和尚于郊野,又附会一联:“修浮桥以孝寡母,杀和尚以报父恩。”看到网上的此类文字,较之家乡的传说,觉得有些庸碌,原来要写此事件的美感,瞬间烟消云散。又到另一座桥上观看,那是我更为熟悉的八里桥
看一眼尖嘴猴腮“快乐不在于得到多少,而是没有那么多计较。”在荧屏的光中,在三十多人的会议室,我旁若无人的想要说话,要潮湿自己的眼角,但是我知道不同的人在,大家都知道。我相信说这话的陈超英大有人在,就像我深信一代伟人在乡村,查看一位老妪的黑暗的灶屋,掀开锅盖,看到的是红薯菜梗而流泪一样,也相信《白毛女》的观众,忘情的站起来说:“不革命怎么行”。那是一个春天,在南关社区的拆迁办,一个尖嘴猴腮的人说:啥
我是否和你分居发什么短信好呢?“想要相亲,你不理我,独自睡觉;想要分离,情义犹在,已难割舍。”我伏案忧思,听窗外的寒冷中,是一棵叫做柳的乔木,正被铁器,一音一音的分裂。我抬头凝神,电脑银屏留驻蓝天下的雪树,那是北方;含露的绿芽,那是春色,含苞的,绽放的,那叫做桃花。我翻开那本红色封面的词集,找到那一句话: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而我无泪,只有沉默。如若和另外的女子打电话,微言我的眼色和心思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更愿意在路南的那幅报栏驻足,顺便浏览一下本市当日的新闻,而不是路东。但是今天步行于微寒的风里,至此却无法观看。一位妇人,高挑的着紫色棉衣的妇人,很熟练的夹好一侧应该是当日的报纸,然后依旧熟练的取下昨天的往事。她不及回头,我却记下了她的背影,她应该是三四十岁的年龄吧,她的孩子有多大呢?是干什么的呢?她的男人,她的父母亲戚?她以此为生计,以此奔波在这个小城,收拢一街一街的
谁删掉了我的工作群睡了一个好觉。昨天已晚,干脆不回去了。门卫老纪少了红薯稀饭,一碟儿地里的萝卜:后院一分多地撒下的种子,由于地浅,只是单位门口修路,协调了几车的铲土。薄薄的一层,没有深耕,小白菜、芫荽长得旺盛,也是满畦的樱樱红萝卜,结实只有拇指大小,最应喜人的菠菜,也是稀稀疏疏,白萝卜只三寸多些,但是极甜,应该是水萝卜,放一点儿醋,还算可口;西红柿炒鸡蛋,再配一点儿泡的药酒。已经是很丰盛了。他四个
燃灯人疏林之间,高台之上,鸟鸣微风,灌木飘香。我于亭榭西面,闭目沉静,回归自我,意守丹田。调息之际,意念先行,只丹田而发,经会阴,底至双足涌泉,意气引领,回至丹田;从双肩向两肘,致手掌劳宫,宫宫相对,相视相通,若窗窗户望,如对岸问答。其波段自然有水的温柔,更虹桥的色彩。其气蕴悠久,不用多时,双足踏地如柱,深入黑暗的土壤,根系于地气相通,一棵树生长在无人的亭台,然后上至百会,在头顶的地方,星光照耀的
黎明前的黑暗他极其感性的表述了对世道的失望,王道昏暴,外族入侵而受凌辱,国已不国,道已非道,吞并战争,尸首载途,此其切肤之痛,抒情泗流:“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依然是腥风血雨,身经百战的另一些将士,则是不同的感慨和愤吼之声。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平实无华,质朴而坚正。比如冀东的根据地开辟与失败,则是“开辟与反复”,应该是悲伤悲愤的回忆,但那字
长泪已殇——纪念我们纪念的你的手翻扬不知那是翅膀一个春天大地夏收万叶秋唱你的眼看我不知那是悲伤一个时代与那潮汐遥迢月光你的脚步啊!我的痴心妄想泪泪行行酒酒醉醉长歌当哭气宇轩昂你一首在心已重天之殇鱼化鸟儿昆仑三江夜夜未央我歌我唱我唱我殇长歌当哭未央未央长泪以殇我歌我唱
秋叶的慰问忙碌一天的时光,只记得黄叶滚滚,黄的树叶透着微微的青灰;并不强劲的秋风之中,映射出霜白的岁月之光。尽管不起感伤,不觉流年,并无美感。记得时间,上班不能迟到,下班赶时间回家。还好,不是过去的那样,又是打车,或者骑电动车,担心车价,或忧心充电,已经办理了刷证的公交绿卡,从家里出发,几分钟走,便可以坐上公交,下车再走几分钟,到达单位;行云流水一般。如此这般,赶点赶时,从未迟到。工作是忙碌的,但
烦由心生,当于内熄一叶知秋,而我楼道里却有一枚枯叶,应该是从丈外的办公室窗外飘落进来,不是秋的静美,而是那枯萎的飘落之声。说无意,却有心;一声传情。也是我晨间上班的途中,于落叶之间,听到路墙之外的堤岸上,那柳枝之间的低语,传来秋至的消息,是萧瑟之意;此有生,若无情。后者是欧阳永叔为其而作的《秋声赋》,因此声在清晨的喧嚣的街头,无人倾耳,只独居无欲的厅室,有正与寂寞之中的远人近神的交谈之间,听到那稀
商桥忠墓应该是在80年代,在许昌市第一中学上学,距离所住的水泥厂家属院有些远,中午便不必回家的时光,可以在附近各条街道和小巷里闲逛。对于一个刚入学的进城的十岁的孩子,一切都是那么神奇,而更多的胡同和小巷竟然是相通的,总是柳暗花明,别开生面的清虚街,衙门后街衙门前街,大十字街,小十字街;老许昌的街道。最爱去的是南关大街,那里不仅仅是本城的繁华大街,而且那里有自己由衷情感的去处——书店,令人惊讶的是,
 如何使用币安Launchpad和币安新币挖矿以及它们的区别
如何使用币安Launchpad和币安新币挖矿以及它们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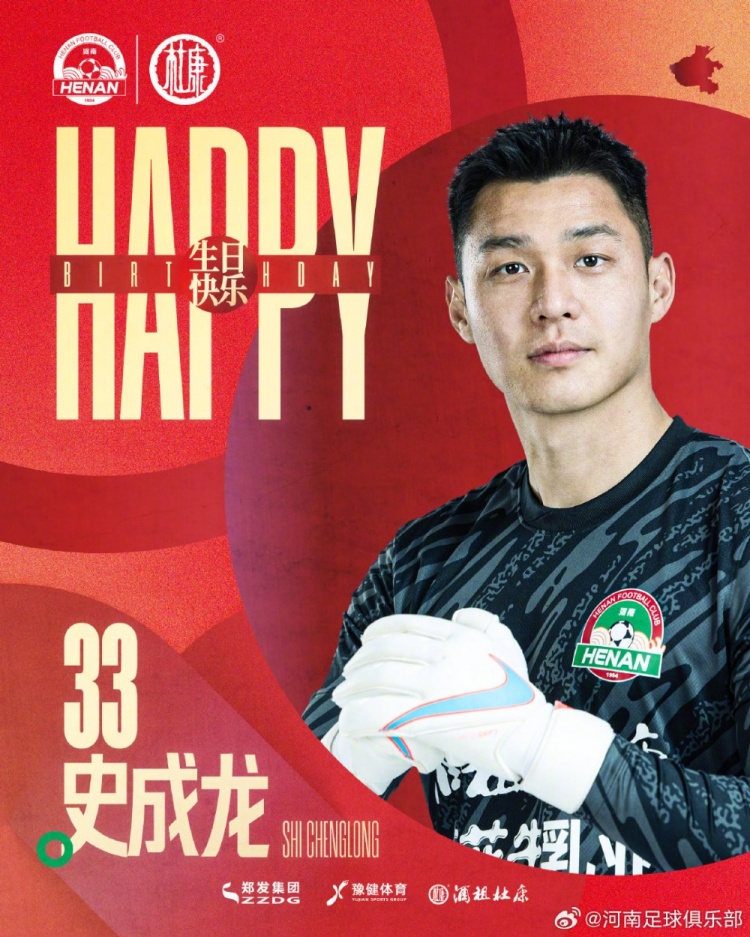 今天是河南俱乐部球员史成龙的生日,让我们一同祝福他生日快乐
今天是河南俱乐部球员史成龙的生日,让我们一同祝福他生日快乐
 提前打卡!特纳8投5中砍下13分3板3盖帽 最后时刻6犯离场
提前打卡!特纳8投5中砍下13分3板3盖帽 最后时刻6犯离场
 币安Launchpad是什么意思?币安launchpad规则
币安Launchpad是什么意思?币安launchpad规则
 夺欧联也留不下?镜报:澳波希望继续执教,但预计仍将在夏季离队
夺欧联也留不下?镜报:澳波希望继续执教,但预计仍将在夏季离队
 威尼斯总监:将花150万欧买断国米门将F-斯坦科维奇,但不留拉杜
威尼斯总监:将花150万欧买断国米门将F-斯坦科维奇,但不留拉杜
 USDT0:泰达稳定币帝国扩张的新节点
USDT0:泰达稳定币帝国扩张的新节点
 收入翻百倍!巴西五人制女足球员遭开除,因被发现成人平台做内容
收入翻百倍!巴西五人制女足球员遭开除,因被发现成人平台做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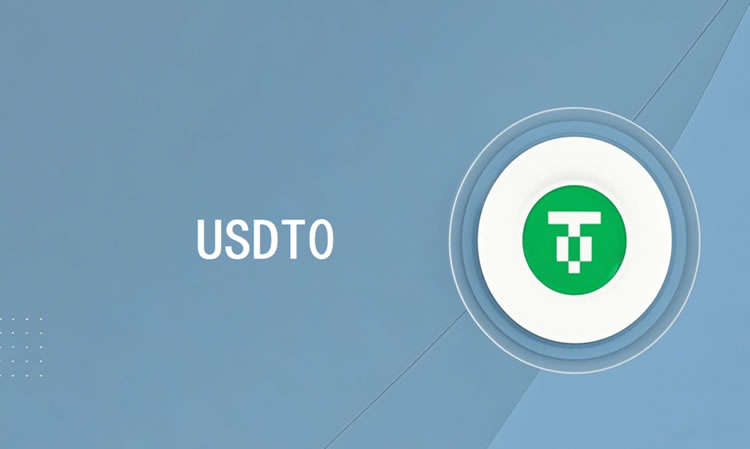 USDT0是什么币?USDT0与USDT有何不同差异?
USDT0是什么币?USDT0与USDT有何不同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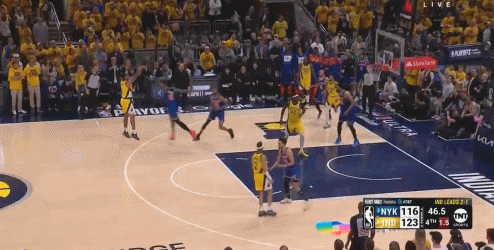 杀死比赛!哈利助攻托平压哨三分!步行者45秒领先10分
杀死比赛!哈利助攻托平压哨三分!步行者45秒领先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