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谁的昨天,没有伤心难过,指尖划过的温柔,我们独自学会消受。缠绕到打扰,中间深爱隔着多少,所有的思念,变成看不见的灼烧,恒久。我爱你,就爱你。
让你入夜难眠的人是谁?让你食不下咽的人是谁?让你分秒思念的人是谁?让你肝肠寸断的人是谁?真爱就该是下地狱的罪?还是没有轮回的心里的鬼?心中装着世间的太多美好,非要全盘托出将其焚烧?没有任何预告,只好放弃治疗,你的微笑,和我未曾展开的眉梢。。。。。。
像这样,不温不火不执著,蹉跎成定果。你是你我是我,没有交集的感情,不会地诉说起漩涡。我真心的认可,你善意地诉说,美妙传说,共你谱过。
云遮月的光,就像我今天忘了,你是那么忙,怎会顾及我怎所想。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朝向你的方向,我分不清诚恳虚妄。如今简单到清水飘香,只得一人就此携手,朝未来投射幸福的光,你可愿共我欣赏,来日方长,和那写满思念的夕阳。
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你对面,你却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爱是种难以言说的鬼东西,一认真,恨不能将心掏出给你,一转眼,又在冰冷的车站分离。以前看三毛,她说:一段孽缘,是魔鬼的玩笑。当时只觉意境深奥,今天,逼真到大脑的每个细胞。再见是为了再见,无花果,酸甜自知,却一心呵护难取难分难以割舍,问三生因果,你共我几多?
走了多久,见了多少新欢旧友,老生常谈还是惊喜不断,都是东升西落岁月流转。不停地奔走,也不全是前进的自由,自己感受。放生自己太久,需要寻回问候,昨天如何,今后怎样,随意而坦然,心思初现。
世间事,总如此,十分热情百倍信心,一盆冷水入神经,避不可及,躲不可起,还得迎难而上笑容可掬,打不死的小强,活的最为漂亮。
狂风肆虐,是不见五指的夜晚,我蹲在田陇上,努力去看清自己的理想。那是个充满阳光的地方,那里的气氛水墨丹青,那里的人们和气安详,那里就是天堂,一个梦一样的天堂。可是,眼前全是狂沙,我已经来不及躲藏......
花开不一定结果,分开不一定遗忘,我在夕阳下的街角,寻觅你长发飘过留下的味道。那是梨香扑鼻,难言的忧伤,带着我的期盼,飞向别人的床。溜走的年华是掉落的头发,风干泪湿的脸颊,我向暗夜诉说着旧日情话,它却回应我天生就傻。想念不是错误的表达,又何来了无牵挂?
日落西山灯火候,石桌四坐满樽酒。风雨乾坤喜乐忧,举杯皆是月影头。
今天,你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吃饭有没有思念?有没有洗碗有没有想后思前?柳絮在风中飘转,小草继续冲击着地平线。请告诉我你也前进了一点,是的,哪怕是一点点...
向一个世纪的时光,洒下自己的卑微理想,在信仰的肩上,喊出心底的愿望。这个战场,我不服输,也不遗忘,你可与我一同翱翔?
天微微亮,人们在睁眼间开始匆忙,胳膊互相碰撞,有时道歉有时不声不响,轰鸣的车辆把人们吞进心房,又吐在不同的街上。我们举目张望低头默想,遇见熟人烟卷飘香,打火机互相诉说着各自不痛不痒,也许我们都鼠目寸光,把那些虚幻的光圈当做方向,一路奋斗一路调整隐形的翅膀,只有自己知道它能否飞翔。春天的阳光给人希望,你依然可以大胆开窗。岁月给你遗憾记忆给你感伤,嘲讽与流言曾让你乱了主张,心平气和不要多想,嘈杂纷乱来
剪刀石头布,你赢我又输,春又来,风又来,燕子又来,我又来,厌倦又来,灯火星光还在。石头砂锅水,白雪远了,棉衣远了,寒流远了,家乡远了,你远了,水落石出,打破砂锅,见底了,猜透了。
来,再来一口,黄土被雪水浸透,我把饭塞进大张着的口,听说你近日消瘦,忘记了维生素和奶油,锅里冒出白色烟幕,那是水的骨肉,在夜里悄悄溜走。一口一知己,筷子我和你。
匆匆一日,匆匆一年,坚实的脚印下,没有绚丽多彩,那又如何,天亮而劳,灯熄而寝,噩梦不在环绕,安心就好。行走,行走,路上的光阴总觉不够,终点在哪头,何须多问候,孑然一身,蜚语自随风。
晚饭后,火炉旁,淡淡的歌,浅浅唱,思绪不短不长。天色已昏暗,灯光点点,弹动的手指,敲下舒心。
匆忙依旧,是充实是不朽?是醉亦是罪,余温微微。灯火点点,狗吠人眠,不知天涯共此时,良辰美景未可知,放下提起,转身迷离。问人生一路因果,尘缘几何?
血浓于水,血水相容,我们亲生骨肉,手足难分。素昧平生,同学相逢,我们萍水相逢,至诚至真。打断骨头连着筋,我的弱小,你曾保护我不伤一分;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的无助,你分秒里给我安稳。原来,真的都是兄弟,我更加理解,什么叫真诚待人。
阿拉斯加的冬雪,散落在遗忘时间,汉谟拉比的宣言,刺穿驯化的谣传,谁说生不逢时命运多舛,谁让洒脱劈头盖脸。当维多利亚神秘浮现,当阿尔卑斯冰川溶解,可有人丢名弃权随己愿,不去管人定胜天。布鲁塞尔的浪漫,西伯利亚的严寒,印证信誓旦旦的预言,大不列颠的绚烂,加尔各答的消遣,流放未被包装的真善。当汤加黎明乍现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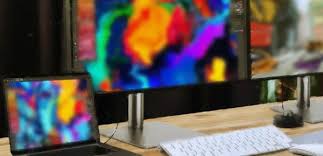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