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孃家我虽没去过,但我知道,就在粮丰顶养猪大户张姐楼前,岔路口左边,一条通往教导团的泥巴路巷子里边住家。汪孃的职业,乡村媒人,信用社小冯、三圣粮站小廖一对是她保的媒。在高店子、黉门铺、乃至三圣公社一大堆妇人里边声名远扬无出其右。汪孃出马,一个顶俩!汪孃与新华村周师娘都是信用社常客,夏天也都常在衬衣纽扣上挂黄果兰,都是搖着扇子一句话三个哈哈,从围墙外痛痛快快打到柜台前的乐天派。路见不平都会灌夫骂座,
与这个未知称谓的大院落擦肩而过,宽阔的机耕道陡然变成为了,被竹林、果园、菜地、秧田包夹其间,窄得刚好容下一人通过的小路。院落一排人家的后屋檐,向外展开依次是一个长方形竹林、苹果园、干涸的小池塘。左边苹果园中的一户人家,家门开在小路反方,屋后一小片苹果树。经年的南瓜、丝瓜、冬瓜藤蔓交替铺开在苹果树、篱笆、草顶间。不时传出一阵有气无力的狗叫。枯竭了的池塘底密不透风铺开上厚厚一层青草、肥猪苗。就连临近过
八〇年代末,高中毕业,通过招工考试,与琉璃信用社曾主任三女儿玉英一道,分配到了那个场镇唯一一所信用社工作。担任储蓄记账员,月薪125元。曾担任对公记账,待遇相同。那个曾经造访过的牲畜市场,包括坍塌一地砖头的豁口,依然和儿时一模一样。水塔外壁一圈黑绿相间的苔藓间,从生出簇簇随风摇曳的杂草、株株纤侬的蕨类,却没了缝隙渗水的滴答声,地上的滴坑也早已被岁月的风尘抚平。巷口高高电杆上那盏老朽于岁月中锈迹斑斑
站在高高板凳或任意一个台阶,铮亮、锋利的(尖刀)刀尖轻触上齐胸的蔗尖,目不转睛,陡然撒手间,电光火石般,尖刀在甘蔗上方疾速划出一道圆圈,迅雷不及掩耳猛切下去!针落有声的场地上,立在原地的甘蔗,如最初般,完好无损,纹风不动!莫非,失了手?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呼啦,裂成两半爿,哗啦倒地!啪啪!鸦默雀静的现场,心儿提到到嗓子眼儿的诸位,如梦初醒般,点头咂嘴,喝彩叫绝,掌声不断,经久不息!每年初一一大早,
如果说,狮子山头没有兴高采烈追逐过轰鸣的蒸汽机车,寂寥田野里牵扯长长风筝线迎着迅猛的东风一路狂飙,大观埝一个猛子扎到底再睁开眼睛有的放矢,哑巴堰边狗刨边心怀鬼胎偷觑岸上累累果实,杀猪房过屠门而贪得无厌大嚼,糖果铺垂涎欲滴目光呆滞,邮电校、生药厂调虎离山翻围墙智取威虎山。三家村顺田埂游戈的煤油灯火里少了你蹑手蹑脚的身影,石灰桥不曾去闸门顶哎哟连天狂轰滥炸,岸边心花怒放煮筒筒饭,四处农田里声东击西偷红
老街两旁稀稀落落栽有几十年树龄的老梧桐树,夏秋季节会掉落到地面不少毛虫,深受其害的人们尽量绕开走。尤以峨眉自行车厂和蔬菜公司门前更为稠密,粗壮。只要不惧怕毛虫,其实夏天到下面乘凉非常舒爽。沿街不少居民在门前用竹竿圈拦一片空地,摆放上各式各样的容器,洗脸盆、罐子、破碗、马桶子,再栽上葱葱白菜、花花草草,只是飞扬的尘土会让一切鲜亮的花朵黯然失色。居民的住房参差不齐,有高低于街面半火砖半蔑夹墙的瓦房,有
每年春节,儿子毛毛会体贴入微牵上汪大娘到家里来过年。体态臃肿的汪大孃犯哮喘,矮胖的身体让一双老腿难以负荷。出门一只手拄拐杖,另一只手腕挎个黑色人造格手提包,到家来不过四里路,走走停停得耗上半小时以上。孝顺的毛毛总是蜗行牛步,随她的蹒跚而蹒跚,牵上她,边陪说话,边一步一回头,三步一落脚。后来很多年才闹明白,汪大孃是九眼桥婆抱的孙女,和笑口常开的田大孃一辈。匪夷所思的逻辑,把比父亲大至少三十岁的汪大孃
对于好高骛远的年青人说来,沙河堡只是成都东门外一条毫不起眼的老街,一条可有可无的烂巷子,一个一夜暴富前必须要遮风挡雨的鸭儿蓬蓬而已。和城里人谈论起家宅的时候,他们多是遮掩、支吾、搪塞。对他们说来,这个荜门委巷破瓦寒窑的一失之地都羞于起齿,明摆就矮人几等!烂摊子、烂巷子、烂棚子、烂房子、烂衫子、烂袜子鞋子,烂得来下啥漏啥,遮哪儿哪儿漏。上趟城就给他妈上老山前线,拿起青春赌明天!九死一生挤上去就怕留不
工作以后位,我前往拜访过他及家人好几次,他赶车到过沙河堡家里一次,和读书那会儿一个样子,拖起直奔甘蔗地。啃得、谈得也如同学少年那般开心、痛快。依然是并排坐在他家后屋檐甘蔗地旁空旷的田埂上,透过坍塌的屋顶,老邓家几间一地瓦砾的土圩子蛛网尘埃杂草丛生。低着头,满脸通红,不停用刀戳裆前的泥土,还是那般谈笑风生,昌言无忌。通红的夕阳下依依不舍,依依惜别,即将翻越狮子山铁轨回头时,家人依然站在坝子,他冲这个
川师大小小一个后门口不知哪年在革委会眼皮子底下竟然和平演变成为了一个超级自由市场,原本五米宽五十米长度与狮子山菜农互通的一条便道被鸡争鹅斗买卖双方拥堵得水泄不通。少了磨牙凿齿的门卫撇秤杆子收秤砣歼一警百,不知猴年马月早成为了不买菜就是一只苍蝇也休想从老子眼皮子底下逃过的新马奇诺。就像被文明的消毒水一次便染作红眼病饮泣吞声师大附中印刷厂二五月临工(25元/每月,时下甲秀0。65元)墨镜(电焊工用)男
异地功亏一篑后,足不出户休整了整整两年余,纵使天大不甘,在余额晃晃悠悠下滑到个位不保那天之前,也还是甘回了被金钱继续奴役的命运,再又干上了待价而沽、见兔放鹰的抢单生意。一月许,终于不堪避坑落井鼻泗横流者,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停下来火中取栗!消沉月余的那日夜,关上房门,偷偷打开电台,调低音量,隔岸观火。依然谈虎色变,危在旦夕,依然贼心不死,不离不弃。正应验了那句箴言,只要有哪怕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就免不了
另一个搅面房位于沙河堡上街邮电所隔壁,一道高高的水泥坎上。与街对面高不可攀十数级阶梯上的沙河堡医院门对门。而要去到这个闹市里的搅面房实可谓魂亡魂失举步维艰。首先你必须得抵挡得住在那个乡村搅面房沿途所勿须担忧来自馆子、糖果、供销、百货各个店面铺天盖地的种种诱惑,其次,很可能在路过那个“让梦想尽可能照进现实”毫无立场可言的人民收购站时你就会八爪挠心意乱情迷,狗日的,假破烂都收,得不得收面粉呢……小供销
马路边这几个生产队都种小麦,可竟然没有一家有搅面房。包括半边街、马家沟、街头好些个国营单位、部队、学校、研究所里凡事不求人的老大哥老太爷,哪天突然想起搓顿臊子面或者包顿水饺他都得因人成事。你总不至于瞧不起豁皮就昏了头牛逼到非得要自己用对窝去舂面粉吧?生产队这两个搅面房在沙河堡可谓风车斗转如日中天。一个出邮电校大门右拐,顺万年青缺口下到墙根儿、排水沟间的一条草径径直走上三十米,左拐,生产队露天化粪池
卢家在生产队忠孝仁爱以俭养德有口皆碑,天资聪慧的老六,是卢家众多男丁中最为得意的子嗣。严格说来我认识时候的他,还谈不上一名合格的社员,只是川师附中高年级一名普通中学生。比校友老大年长上半岁,哑巴堰苹果园边上一个土坯四合院住家。十六出头,瘦削,干练,性情温和,踏实、谦逊,长年三七分,脸上些许雀斑,1.75米。匠人六平常休息或放学后如果不割猪、牛草、扒柴禾,便会在居家门外土坝子摆摊设点扫榻以待。一把推
辞职以后,狮子山豆腐块儿菜地偶尔转转,几乎足不出户。时常也会按奈不住楼下路边摊色香味的诱惑,却照旧很久没有在行道树旁众目睽睽下收紧菊花才敢试着靠上去的小塑料板凳上点过要啥缺啥的免锅底手提plus,再怡情悦性哼哼情歌调调小酌上一杯冰镇黄货。更不曾奢望一盆正经八百麻辣鲜爽、异香扑鼻的非转基因鸡油火锅。尽管那次在彭州南门另一个路边摊犹豫数日后终于鼓足勇气靠了过去,16。8元/花鲢/每客,10元/锅底/每
满城风雨的那天,锦里古迹提心吊胆刚下完客手忙脚乱换好挡正夺路而逃,砰,一声门碰,后座跳上满头大汗金体恤金项圈。交尾、便衣、密探、线人、007一股脑惊悚闪过!“双流机场多少钱?”一口非本土方言普通话。平白无故跳上私家车,白色恐怖目的地,更断定了某的忖度,舶来神探!一定是张网以待诱敌深入的幌子!接下来不消说都是几点几、几十几、几百几道琼斯无穷魅力指数节节飙升!溢价,大大的溢价,1000倍数溢!再接下来
次日荣边镇缝场,事前我并不知晓。一大早那条向来很会察言观色的黑狗狂吠不止,阳台上见贵生啃着梨儿提个塑料口袋,里面几个黄澄澄的果子。捏上一截竹竿面露怯色战战兢兢蹬上石阶来到院子,只手长长递出口袋。女主人三两步蹿上近前接过口袋,“嗨呀,你还客气啥子嘛?嘻嘻嘻嘻,还讲理得很,专门赶场买。”,边招呼贵生院里落座。“嘻嘻嘻嘻,贵生……”。甚至我都没有心思再和贵生客套便急返回房间,重重摔出一声狗屁不是的门碰。
贵生,这个就连生产队公认最缺心眼儿的王豆儿都热衷于说长道短的角色,刚来那天就成为了主人家饭桌上津津有味的下饭菜。五十出头,单身,本土第一猥琐男,整座尖山最多情一棵种子,只要见钱就眼开,只要喝酒就没够,只要异性就想入非非。管她半老徐娘,还是人老珠黄,在贵生这头种牛瞳孔里就是如花似玉的粉子。他才不会计较你脸子怎么样,天生还是后生缺啥陷不陷的,在他雷达可视范围从来就没有过一头一尾,纳米波段仅限脖子以下大
虽不懂芳花的情感,却不失志趣品鉴,窄窄的阳上,我密不透风摆上了好几盆鲜花。老妈房间里电视柜、咖啡桌、小板凳也摆上了唯独一盆赏心悦目的高贵草花。只知道属于兰本,但绝对不具有幽兰的神采。繁花似锦、活色生香,一看就绝非某阳台那等萝卜、白菜。不要妄想可以陡然揽获竹荫、山涧暗香浮动的欣喜,更不要指望丢哪就在哪里发芽开花吊兰的胸怀。纵使在三个地方来回挪,来回惯,来回迁,来回侍候,千种呵护,万般疼爱,就差没放在
其实,我热爱怒放的花朵,厌倦秋风的萧杀,憎恶严冬的冷酷,怜惜鲜花的凋零。我不知道,那会是一双怎么样子邪恶的黑手才能忍心去把鲜亮的花朵从翠绿的枝头偷走!往年,在不经意间也曾看到开过的花儿,炫耀的白变成黯淡的黄,折皱,蜷曲,在无奈的等待中挣扎,煎熬,枯萎,干瘪,凋零。抚景伤情,逝者如斯,多希望青春的花朵永远绽开在翠绿的枝头!我欣赏兰花,花中仙子,玉洁冰清;迷恋茉莉,莹白如珠,幽香袭人;然而,我更热爱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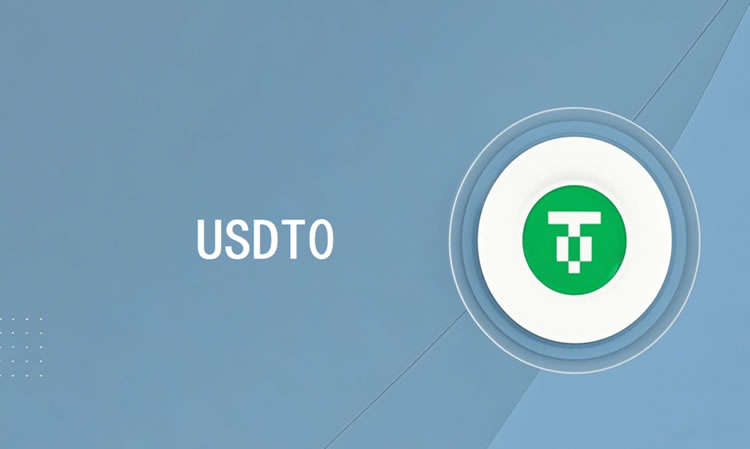 USDT0是什么币?USDT0与USDT有何不同差异?
USDT0是什么币?USDT0与USDT有何不同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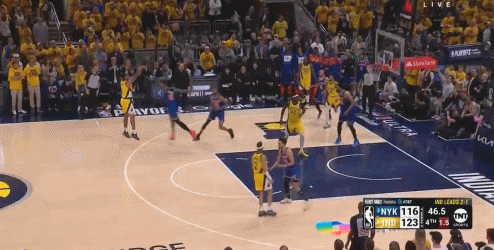 杀死比赛!哈利助攻托平压哨三分!步行者45秒领先10分
杀死比赛!哈利助攻托平压哨三分!步行者45秒领先10分
 币安的P2P交易在哪里_币安P2P购买USDT的流程是什么
币安的P2P交易在哪里_币安P2P购买USDT的流程是什么
 从被嘘到逆袭!队报盛赞法比安:低调优雅的中场,用表现赢得认可
从被嘘到逆袭!队报盛赞法比安:低调优雅的中场,用表现赢得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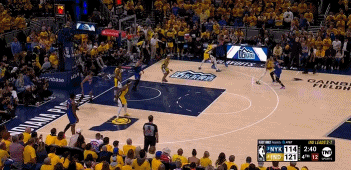 立功了!内史密斯提前站位造阿努诺比进攻犯规
立功了!内史密斯提前站位造阿努诺比进攻犯规
 如何在币安成为商家?币安商家的保证金是多少?
如何在币安成为商家?币安商家的保证金是多少?
 沙特U16队主帅:中国队是很强的队伍,我们会展现最好的状态
沙特U16队主帅:中国队是很强的队伍,我们会展现最好的状态
 数字货币交易app排行榜前十名 数字货币十大交易平台最新排名
数字货币交易app排行榜前十名 数字货币十大交易平台最新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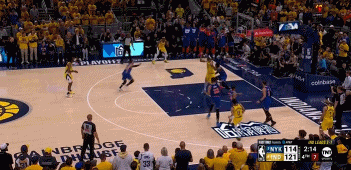 唐斯补防内史密斯双双倒地被吹防守犯规 尼克斯挑战成功特纳推人
唐斯补防内史密斯双双倒地被吹防守犯规 尼克斯挑战成功特纳推人
 兰德尔:在尼克斯打球没意思&无法专注于比赛 狼队让我有归属感
兰德尔:在尼克斯打球没意思&无法专注于比赛 狼队让我有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