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卑微淳实的父爱父亲在我参加工作不到二年就去世了,距今已整整37年。时间如流水,时刻冲刷岁月的痕迹,许多的记忆已经朦朦胧胧,只记得父亲去世那天是中秋节的第二天,灵棚外面的月亮很白很大……父亲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木工,现在的泥木工月收入高的可达上万元,而那时候建筑单位的泥木工的属于收入比较低的工种。父亲在儿女面前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面孔,他嗜酒吸烟,印象中的父亲总是手里端着一个酒杯、周身烟雾缭绕。现在仔细思
10、坐邮车我的家庭按现在的说法是应该划到弱势群体中去的,父亲是建筑单位的木工,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靠做些临时工来争些钱以弥补家庭开支。在下乡的年月里,我们每年一般只回来一次,就是每年的春节,父亲的单位派辆大货车把知青们全接回家乡,过了元宵又把大家送到农场。在我的印象中我中途回来过两次,一次是我兄结婚,我是爬车回来的,一次我病了,是单位的救护车把我送回来的,休息几天还是要回农场呀,搭班车是舍不得
9、回乡路遇兄要结婚了,我在农村接到喜讯,高兴极了。我兄三十而立,解决婚姻大事,是家中多年的夙愿了。我通过武冈知青的关系,把自己积蓄的20元人民币买了四条精装的上海烟,而把自己回家的费用给忽略了。我约好知青朱,用知青们的惯例:爬汽车回故乡去。天刚蒙蒙亮,我俩便出发了,一个时辰才到县城。走过县城,我们就爬上了一辆邵阳市商业局的汽车。那车是七十年代我国从日本进口被称为“日野”的货车,车厢低,速度快,但
精神荒漠中的一群狼写下标题,总感那“狼”字用词不当。在当知青的岁月里,是没有什么精神文化生活的,所以把处在几乎没有精神营养供给状况的知识青年比喻成“狼”了。那时如果听说某地方放电影,那怕七、八里路远,知青们都齐齐浩浩地跑去看。在我的记忆中,看得最多的电影名是《南征北战》,百看不厌。有一次,我在大队小学一位校长家里竟然翻出一本《史记诠释》,当时,那位慈祥的女校长都有几分诧异,她十分慷慨地把书送给了我
营养匮乏症(1)偷肉记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知青们的生活十分艰苦,每月打一次“牙祭”,每人半斤或一斤猪肉,一餐吃得干干净净,大家只争肥肉,越肥越好。想现在人到中年为应酬酒宴快吃出胃病了,恰应了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呷得时冇得呷,呷不得时万千的呷!”真是感慨系之。我们几个知青在农村偷肉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颇有几分意思。那是1976年的冬天,我们已经吃了一个多月的“红锅菜”,何谓“红锅菜”?就是不放油
4、“落户”与“春插”1976年的春天,我下放的时间不到半年,由于“抢劫案”一事在整个农场和大队造成了极大极坏的影响,我因此仿佛成了一堆臭狗屎。每个生产队都拒绝接纳我的户口,我们知识青年都是在农场干活,在队里分粮,于是我便成了一个既无户口又无口粮的“黑人”。对自尊心很强的我来说,心口无异于被狠抽了一牛鞭,我的自尊感荡然无存,而自卑感却到了极点。马上就要下生产队“春插”了,场里的知青全部到自己落户的
2、最后一片秋叶…………(本篇见古榕树下网站“作家故事”)3、“抢劫集团案”我下放在人称全国“七十二福地”的第六十九福地——武冈云山脚下,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云山顶上存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森林里经常有豺狗和野猪等野兽出没,山下有一座大水库,那水绿得象青苔似的。水库的水经过一条渠道流过我们的村庄,一年四季象一条清澈而永不干涸的河,我相隔十余年后再返此地时,山上几乎全是人工林,那些个野生动物已绝
序言我的履历表中,生活经历一栏首条总是如此填写:1975年——1979年“上山下乡”务农。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对这段经历我只能鼓起自己虚弱的勇气去回忆;犹如去挖掘一口快要成功的水井,只要稍微刨开一点点土皮,水便会汩汩地冒出来,倘若又去猛掘二锄乃至三锄,则自己就会被爆溢的井水所淹灭,留下无限的悲哀。然而,直至今日,如果晚上偶尔做恶梦,便一定是身在农村、又是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夜陷于那无
来长沙已经一月有余,有许多的感慨和领悟,人云:“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在长沙的一些经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此话怎讲?容在下慢慢道来……按理说,某人今年61岁,尽管年纪大了些,但也是个走南闯北的人,除了新疆,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国外也去过三、五个国家,曾记否,在澳大利亚,与团队走散,独自一人,结结巴巴地用蹩脚的英语单词逢人便说:“爱艾麽
南国雪(第二十章)十年后。刚刚入冬,北京已经寒风凛冽。和妻子坐在客厅里,电视正在播放西北地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画面。“今年冬天比往年来得早。”我自言自语。妻子发下手中的报纸,把眼镜拉至鼻尖,通过镜框上端眯着眼瞧我:“你说什么?”“我说今年冬天会很冷。”“哦……对了,近段时间忙不?”“还行。”“趁南方还不冷,抽个时间去一趟南国吧。”“去干什么?”我盯着妻子问。“去看看肖剑平,他的案子已经结案了。”
南国雪(第十九章)尽管几十年不遇的冰灾,除了一些绿化地带还存留着一片一片白雪积冰,南国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各个街道被突然冒出来的车辆堵塞,公交专用道的公共汽车一辆一辆来回奔驰,被雪水浸洗后的城市在缓慢地苏醒并逐步恢复生气。门铃响了,刚好晚上八点,约定的时间,肖剑平还是蛮守时的,拉开门,肖剑平爽朗的笑声先传了进来。“呵呵,老兄呀,这两天辛苦啦,我没陪你,对不起啦。”肖剑平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位穿着朴质,
夜已深,睡意却无,百无聊赖之际,翻开多年尘封的日记本,那是四十多年前写的一些所谓的"诗”,那文字,尤如当年十六、七岁的我一一青涩之极,却也可以闻到一点当年那种偏激的政治火药味。看那些个”诗”,倒也别有一番趣味,依稀记得当时自己很为这些文字而自豪,并以这些个东西为本钱而自诩为文学青年!要不然为何能认真地把它们记载下来呢,现摘录几首,曰:奇文共欣赏……《“十大”喜讯传四方》1973.11.1
南国雪(第十八章)短短几天时间,感觉自己在时间的隧道里来回穿梭,在多维空间里跳跃悬浮。从雪陵山区回到雪陵市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尽快与青青见面,许多事情需要得到落实和见证。特意交代接待处:不要车子接送,不要人员陪同,根据青青电话里说的地名,我打的来到雪陵市建筑公司家属区。才下车,远远地就看见青青像燕子一样地向我飞来:“青叔叔,青叔叔。好几天了,好想叔叔!”她拉着我的手蹦蹦跳跳,我十分爱怜地抚摸她
南国雪(第十七章)清晨,太阳费劲地挤出云层,匆忙射出无力的光芒,更多的乌云如失职般地即刻涌来,把太阳遮盖得严严实实,经过雪水和寒风的洗涤,雪北县城的空气格外地清晰。罗县长早早守候在餐厅,就餐的人稀少,整个宾馆显得清静而安宁。主宾在餐厅坐下,却发现罗叔不在。“罗老呢,昨天没在宾馆休息?”我皱着眉头表示自己的不满。“他早上回去了,说是拿什么东西。”罗县长解释。“哦”,记得昨天晚上罗叔说过,要还我什么东
南国雪(第十六章)1979年初春,整个大地春意盎然,山峦、田野、河流处处传递着春天的讯息,尤其是我钟爱的梅花,在漫山遍野里缤纷怒放,红色的梅花如烈焰般艳丽、白色的梅花如洁白的雪花、绿色的梅花如嵌在银色花盘中碧绿的翡翠。我明天都要采摘一朵梅花放置我的房间里,用泪水把它浇灌。二月,知识青年可以回城了,许多的知识青年像涓涓溪流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雪北县火车站的旅客几乎都是返城的知识青年,大家喜形于色,互
一我喊王印堂“印舅“,他是我母亲的表哥,严格来讲:他应该是我的表舅。提起王印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分别见过一次,高个子,长长的马面形脸,两眉之间、眉毛与眼眶之间相隔的距离很宽,给人以稳重、睿智之感。我母亲对他评价经常用这么一句话:我们的印哥,那是个厉害角色呢,是个“三开干部”!何谓“三开干部”,母亲的解释:在国民党手里吃得开,在日本人手里吃得开,在共产党手里同样吃得开!有次我与一位很有文学
南国雪小车行驶在山区的公路上,公路蜿蜒而曲折,车窗外,南国冬天的雪景宛如一副素雅的中国画:茫茫林海披着素装,绿白相间,层次分明。前面的警车顶上的警灯在无声地闪烁,路边的行人稀少,一些没有被雪遮盖的黑土地稻田和裸露着,一派荒凉的景象。此次返乡,原本要去雪陵山祭奠海红,却遇上了海红的女儿,事情的变化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回故乡的目的一下子变得茫然,心情也慢慢抑郁起来,快到知天命的年龄,对自己已经非常了解,
秋风渐凉,总是在秋天的日子里最挂牵自己的亲情,想我那外似强势,内则柔弱的女儿在外面打拼,时时揪神担心,做父亲的我老是为自己不能为女儿提供坚实的羽翼而自责和自愧,用鞭长莫及、爱莫能助、心有余而力不足等词语均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心境。也是那年秋天,你去北京求学,我去火车站送你和你母亲,天灰蒙蒙一片,隔着车窗,父女俩说着话……火车“乌”地一声鸣叫,你一下子扑在你妈妈怀里哭了,是呀,女儿是第一次离开父亲去
南国雪屈指一算,元旦节快到了,自己已被监禁1个多月,听那审讯我的公安人员讲话的口气,我的案子似乎快结案了,如何定罪,是凶是吉,自己也无法预料,只好抱着听命于天的态度了。元旦节的前一天,天才麻麻亮,看守所大院了传出嘈杂的声音,厉声的吆喝,步伐整齐的脚步声,口哨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提到嗓子眼上来了,一会儿,牢门打开了,进来两个解放军战士,不由分说,五花大绑地把我扎扎实实地捆了,来到大院,几辆警车和
南国雪(第十三章)来到雪陵第三天的清晨,我早早就起床了,在宾馆的四周走了走,地面上的雪已经开始融化,房角此起彼伏地滴着雪水,大概融雪的缘故,寒风吹来的空气清新而寒凉。在一位自称“接待处长”的中年男子陪同吃完早餐,回到房间,我在房间里轻轻地走来走去,仍旧思考着自己回到故乡来所遇到的人与事,想得最多的青青,从青青出生的年份来讲,这个女孩子或许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该念头在脑子里闪现时,总会有种说不出来的奇
 阿尔特塔:我们确信能够应对任何情况,并且会享受对阵皇马的比赛
阿尔特塔:我们确信能够应对任何情况,并且会享受对阵皇马的比赛
 选择贝勒大学!经纪公司:邓雨婷收到60多所NCAAD1大学的转学邀请
选择贝勒大学!经纪公司:邓雨婷收到60多所NCAAD1大学的转学邀请
 曝知名零售商每店只有100台Switch 2:游戏与配件更稀少
曝知名零售商每店只有100台Switch 2:游戏与配件更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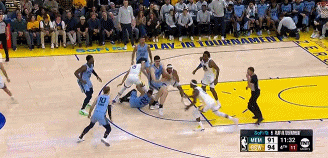 贝恩三分+康查尔反击上篮 灰熊第四节初反超比分!
贝恩三分+康查尔反击上篮 灰熊第四节初反超比分!
 梦幻联动!AL官宣与漫威《雷霆特攻队*》联动:英雄已组团,出道在即!
梦幻联动!AL官宣与漫威《雷霆特攻队*》联动:英雄已组团,出道在即!
 Bybit在国内怎么注册?国内注册Bybit的具体教程
Bybit在国内怎么注册?国内注册Bybit的具体教程
 一文详解Bitget如何透过P2P交易进行法币充值
一文详解Bitget如何透过P2P交易进行法币充值
 MoonPay要实名认证吗?需要KYC吗?
MoonPay要实名认证吗?需要KYC吗?
 如何在OpenSea交易所上架、购买NFT?Opensea购买NFT完整教学
如何在OpenSea交易所上架、购买NFT?Opensea购买NFT完整教学
 HTX火币官网2025最新介绍(比特币以太币交易平台)
HTX火币官网2025最新介绍(比特币以太币交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