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严是我校的职工,五十多岁,一副憨憨的样子,负责学校卫生检查。每天早上他像个大内总管,把学校卫生检查一遍,尤其班级,一检查到卫生不满他意的,立马叫出班级卫生干部,组织重新打扫。班级干部一看到他来,毕恭毕敬,心里敬畏着呢。有一天我在班里组织学生背诵古诗,他又来了。他走进教室,四下瞧瞧,看到纸篓内不干净,不问我,直接询问卫生班长邱子豪:“倒完垃圾,为何不用水冲洗一下?”邱子豪还想辩白,转念一想:“虽不
法布尔研究发现,未长成的蝉的地下生活是四年,而在阳光下的享乐只有五个星期。地下生活时间之长,地上生活时间之短,让人惊诧。可是蝉为了一个多月的歌唱,它忍耐、煎熬了四年,从没有放弃对幸福日子的向往。即使在黑暗里摸索的时间过于漫长,一旦阳光照临,那欢喜也无法替代。这种执着的劲头令人肃然起敬。意志不坚定者早就被黑暗吞噬。蚂蚁遭遇危险,尤其火灾,个体不是急着逃难,而是抱团避难。它们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先来在
早晨上班走在路上,看到一位老人右臂擓着竹篮,篮內放着整齐的韭菜;左手拖着拉杆,拉杆上放一敞口口袋,袋内装着新鲜的生菜。让我惊讶的是,他走路很不便,一瘸一拐。这样的老人该安享晚年,还这么艰难地为生活奔波。他真的不容易。我家前面滨湖緹香小区正在施工,我还在睡梦中,机器的轰鸣声就惊醒了我。天才麻麻亮,工人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们带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我分不清他们的性别与年龄。在我看来,他们付出的体力是
看到教室后面的书橱里有本《史铁生散文选》,我一下想起了史铁生这个人:饱经沧桑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坐在轮椅上,面带微笑;还有那一篇篇散发着温情的作品……史铁生离开我们十二年了。他在我心中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不屈服于命运的抗争者,顶天立地;他的文字就像有着体温的血液流到我的血管里,无声无息,却又激荡人心。知道有个作家叫史铁生是在2006年的5月。一个实习生临走前送了本书给我:《命若琴弦》。200
今早骑车上班,在二中西面十字路口等绿灯,短短几十秒就看到四个人骑着电瓶车闯红灯横穿马路,我为他们捏把汗。幸亏早上车辆少,要是上下班高峰潮,该多危险!或许他们很忙,时间无比宝贵,只有闯红灯才能不耽误做下一件事;或许他们没安全意识,路口没有行驶车辆,通过无关大碍无伤大雅;或许他们根本没注意,错把红灯当绿灯……常人犯错再正常不过。四下里无人时我也曾闯过红灯;为了走捷径我也踩过草坪;走路无人时我也吐过痰;
我家住在砚临河畔。自从家里养了小狗之后,我就再也要不到睡懒觉,早晨六点左右,要带它出来溜达,解决它出恭问题。我领着它,它在砚临河边撒欢。除了遛狗和健身的,还有来的更早的:一群垂钓者。他们在淮宝路大桥南边、砚临河东岸,安放好钓箱或钓椅,架起鱼竿,撑好大伞,正襟危坐,目视鱼漂,专注的如同数星星的孩子。我从西岸看到这样的垂钓者,心里有说不出的羡慕。他们这么早来垂钓,真自由,不像我受职业限制。我也是个钓鱼
任何尽职的人,我都会把他送入天堂。我是天地间的判官,掌管世间众生命运。我有自己的审判标准。我阅世数年,判案无数,见过形形色色的人。那天下午我正在天空闲游,突然有个飞行物一闪而过,没多久就开始垂直下落。我才看清那是一架飞机。我惊悚不安。飞机这么落下去凶多吉少。我没有魔法,无法帮助,眼睁睁看着它坠落。不久轰然一声冒出一阵浓烟,飞机遭遇不测!我向下一看,飞机坠落深山。飞机上的人生还的希望极小。这样的高度
马克龙连任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4岁,而他的妻子--他曾经的老师,比他大整整24岁,今年已是68岁的老妇人。马克龙连任成功后到埃菲尔铁塔前庆祝,与夫人手牵手肩并肩,相当亲密爱恋,叫多少人羡慕嫉妒。我不理解,年轻帅气的马克龙不找年轻貌美的,而娶了个比他大那么多的老女人,颠覆了很多人的观念,也让我质疑了很久。这个女人不简单,肯定有手腕会魔法,有过人之处,把马克龙牢牢地抓在手中,过起了法国第一夫人的高
清明节开车回老家,发现通往老家的青年路变得平坦宽广,而长在路边的树都不见了。哥说,为拓宽路面,有的树木移走了,有的砍掉了。那些与我的童年有密切关联的树,在我的脑海里舒活过来。农村的孩子十之八九会爬树,那灵活劲儿,赛似猴头。春蚕一孵出,家家忙开了,采桑,切碎,均匀撒在蚕宝宝身上;等蚕宝宝三眠过后,就要高频率地把桑了,这要爬到家前屋后的桑树高处采桑。我们兄弟几人都是爬树的高手,我双臂抱着树,两只脚不停
春天,树也落叶子!那天早晨走进校园,经过小教学楼后,发现地面落了一层树叶,黄色,近乎没有水分的那种黄!我很奇怪,寒冬早走远,春天已到来,自然生机无限,绿色主宰了树木、草地、原野,正是风和日丽、春风荡漾的好日子,怎么会有落叶?昨天天气预报说,冷空气南下,夜间有大风。吼吼的风刮了一夜,一夜之后,地上落了一层树叶。这些叶子来自哪里?我抬头细望,小教学楼后长着一片大香樟树,一一棵挨着一棵,粗壮的枝,浓密的
最近内火有点大,下嘴唇起了火泡,一碰生疼,还严重影响美观。我想买点水果败火。什么水果败火呢?上网一查,梨、西瓜、火龙果、柚子、甘蔗等有明显效果。我上下班经过的街上有不少家水果店,我只会到小波水果店去买。这条街上,我最信任的就是他家。我与小波打交道已有几年,在我看来,小波本分、地道,童叟无欺,老少热情。他初中毕业就开始经营水果了,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小波说话从不拖泥带水,直来直去,分贝不高;黑灿灿的,
总是在没亮光的夜晚突然地醒来静悄悄的世界听到自己心跳的节拍儿时在野外疯玩远远地听到母亲热切地呼唤我哧溜一扭脸发疯似的狂颠为赶上桌上冒着热气的菜和饭而现在我与母亲相隔两个世间二十多年不见母亲还在呼唤和以往一样的急切一样的响亮母亲才是不遗弃我的人清明将至妈妈,我要回去看您您不曾衰老的容颜您不曾硬朗的身体我依然很熟悉我要给您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要把这些年的工作我要把兄弟姐妹们的信息我要把家里的年成和收入还有
撵着撵着冬风,春天就来了。新年过去还没多久,冬风还在纠缠着树木、房屋、河流、荒草和人群,吹在脸上,钻进衣服里,我们并不觉得如寒冬那般刺骨,似有一股力量推着它,催促着它早点撤退。这力量的主人就是春天。每年到这时分,春天不请自到,不宣自任,宣誓主权,让大地回暖,催万物苏醒。春天遵循自然规律又迫不及待,一年之计在于春,是一年之始啊,得做出榜样,为自己证明,所以赶着赶着冬风,自己就现身了,就露面了。春天是
我打记事起,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就没有入过席。一次,我的表叔从外地来,顺路来看我的父亲。父亲很热情,一定要表叔吃了午饭再走。父亲陪着表叔说话,母亲忙着下地挑菠菜,挖大蒜,择芫荽——一会儿装满了大半篮子。母亲一到家就摘菜洗菜,动作麻利,很快清洗干净。到了厨房,她一人既烧火又炒菜,一会儿锅上一会儿灶下。母亲仿佛会分身术,火烧得旺菜炒得快。我还小,不晓得帮忙。没多大功夫,几碟家常小菜端上了桌:涨鸡蛋、咸肉
为何出这样的命题等春天这位教授研习后选定日期泥土怎忍受煎熬呼啦啦一阵春风叫醒沉睡的所有朋友堤上柳绿陌上花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招摇着狂舞着伸长了颈项对着春天心绪不宁有人从花间穿过构思诗篇的人闻着油菜花香摘取一地诗行她是这个季节最充实的富人油菜花开了你该来看我油菜花开遍了水岸花城这阳光般的油菜花如你的眼神穿过寂寞排山倒海你说油菜花开了来看我我等待你的消息漫长的季节里油菜花不败我静静站成一棵树守护花期
忙活到中午,老邱挑着担子走回了家。门还锁着,锅还凉着。他叹了口气,没了老伴,没人照顾,就吃不上热饭。淘米,生火,一个人弄饭一个人吃。老邱有时候觉得生活没意思。生活再没意思,不想死就还得继续。日子如细水在流,不紧不慢,老邱渐渐习惯一个人生活。老伴在世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像个老小孩被老伴照顾着,饭好了,老伴端到桌边;要衣穿,老伴拿到跟前。他从不为日常挠心。老伴突然离世,给他迎头一击。起初他无所适从,
我家对面小区有个爱老院,住着不少老人。天气暖和的时候,我总看到一些老人坐在台阶前的椅子上,沐浴着阳光。他们一溜排坐着,望着东西来往的车和人。浑浊的眼睛竟那么入神,让人动容,像极了我的父母。我不止一次经过,一次又一次感慨,让我有流泪的触动。他们老了,脸上沟壑纵横,眼皮松垮,头发蓬松而花白;穿着一点儿也不讲究,老人款的服装衬得人更没精神;他们有的行走不便,靠着拐杖艰难挪动。他们在期盼和失望中度日。他们
云想衣裳花想容前些天买了一件新衣服,穿上,舒服、得体;学生说,人看起来很有精神,帅多了。我心情愉悦。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狗配铃铛跑得欢。”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穿上自己想穿的衣服,尤其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体会更深。我的大姐比我大十岁,我十岁那年,大姐二十岁,外公特地上街买布料,要给我们做新衣服。几天后,我就穿上了崭新的褂子。穿着新衣站在镜子前,左转右摆,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好像换了一个人。我从没
住处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和另一个单身汉住在一起;后来我结婚,搬到另一间。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砖瓦房,好多间连在一起。一间也就十几个平方,我简单布置,中间帷幕一拉,半边是客厅又是餐厅,另一半是卧室又是书房。厨房前是下水沟,大屋后有树林,远处还有菜地,这环境很适合蚊虫老鼠栖息。盛夏蚊子嗡嗡声不绝于耳;更命的是晚上熄灯后,房顶上成群结队的老鼠如履平地,闹腾得我们无法入眠。为了家中物品安全,为了能睡个安稳
那年的相逢只因诗与远方南北的距离地图上只是一指我轻轻一抬手便可越过我没日每夜地呼吸只想闻到你的气息我在文字堆里不停地出没熬出光秃秃的额头你点亮我整个宇宙我用我所有的能量温暖你每一个日子把明媚的月亮还有那璀璨的星星装点成新房亮成你一生的银河我的心只会为你停留在你我之间我幸福地徜徉不止有诗和远方还有无端的风雨我们学着迎候那一年的相逢奠定我人生走向在情感的河流里我心定如磐不系之舟紧紧靠岸
 阿尔特塔:我们确信能够应对任何情况,并且会享受对阵皇马的比赛
阿尔特塔:我们确信能够应对任何情况,并且会享受对阵皇马的比赛
 选择贝勒大学!经纪公司:邓雨婷收到60多所NCAAD1大学的转学邀请
选择贝勒大学!经纪公司:邓雨婷收到60多所NCAAD1大学的转学邀请
 曝知名零售商每店只有100台Switch 2:游戏与配件更稀少
曝知名零售商每店只有100台Switch 2:游戏与配件更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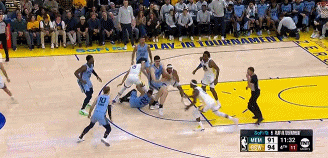 贝恩三分+康查尔反击上篮 灰熊第四节初反超比分!
贝恩三分+康查尔反击上篮 灰熊第四节初反超比分!
 梦幻联动!AL官宣与漫威《雷霆特攻队*》联动:英雄已组团,出道在即!
梦幻联动!AL官宣与漫威《雷霆特攻队*》联动:英雄已组团,出道在即!
 Bybit在国内怎么注册?国内注册Bybit的具体教程
Bybit在国内怎么注册?国内注册Bybit的具体教程
 一文详解Bitget如何透过P2P交易进行法币充值
一文详解Bitget如何透过P2P交易进行法币充值
 MoonPay要实名认证吗?需要KYC吗?
MoonPay要实名认证吗?需要KYC吗?
 如何在OpenSea交易所上架、购买NFT?Opensea购买NFT完整教学
如何在OpenSea交易所上架、购买NFT?Opensea购买NFT完整教学
 HTX火币官网2025最新介绍(比特币以太币交易平台)
HTX火币官网2025最新介绍(比特币以太币交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