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的雾真大!能见度几乎不到5米远,如此的大雾这几年的秋冬简直是太多了,这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呢,还是自然气候的缘故?走在路上的行人,除了两眼紧紧地盯着前方不敢丝毫放松外,偶尔考虑的大概也就是这样的疑问了。尽管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讨厌的雾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喟叹。除了关心自己
单位宿舍门前有一棵白杨树,枝叶异常繁盛茂密,树高十几米,树干直径约六十公分,树冠在半空铺展开来,像一把巨型的大伞遮护着下面的几间平房。虽然白杨树并不古老,但几乎没有人能说清楚它的树龄了。在其周围目所能极处,实在没有一棵树可以和它相媲美,于是它便足以吸引众人的眼球于其身了。我便时常地注目于它,浮想联翩
门外的敲门声传来,我猜测到多年不见的同学小D来了。说是同学,其实是老乡,因为异地读的大学,自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就相识了。尽管不在一个系,见面还是很经常的,于是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因为无话不谈,我渐渐知道了他的情况和背景。原来他的父亲是国营企业的厂长,他是计划外的委培生,当时他父亲的那家
生命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人:母亲,妻子和孩子,这是你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也是你生命的天。母亲是你生命中最亲的人。现在社会,我们都很忙,但是你再忙,也不要忘了你的娘,她生你养你,是不希求任何回报一生只为你付出的仅有之人;你再苦再累,也不要先苦了娘亲,她老了,为你她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停留越
儿子开始离开幼儿园,报名到小学上学了。每年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家长,为孩子的上学生出一些愁怨,因为孩子上学要交一笔借读费,我要交的这笔借读费其实很冤枉的,人家的借读费是因为外地的,户口不在本地而来此就读的,交几千元的借读费虽然多了些,也很无奈,但自己多少有点愿意,毕竟县城的教学设施、教学师资
窑坑老家村北的坡里,有一处窑坑,十来亩的样子,据说是大跃进时用秫秸炼钢铁留下的,但如今已看不到任何炼钢的痕迹了。凸起的土堆泛白着盐碱,坑周围的低洼处杂草丛生,破烂的碎砖块和发黄的土,一道组成了一派荒凉的景象。夏天给人以炎热,冬天给人以凄怆。小的时候,母亲跟我们说,我们就是从那儿捡来的,只要我们不听话
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送我们上学的目的只有一个:能认得自己就行。他们并不奢求孩子将来能有多大的出息,也没想到要孩子考入大学,摆脱世代务农的艰辛。他们希望我们能早日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过上平安的生活。尽管在学校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没有人想到将来有一天我能吃上“皇粮”,因为我们周围几乎没有一人
与妻儿去超市,看到在超市的过道门口处,瘫坐着一位白发苍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头,他的面前是一把破旧掉瓷的搪瓷杯,那是他盛放行乞来的钱币的,也许那还是他吃饭用的工具。走过他身旁的男男女女看也不看他一眼,谁要是给他一目光,他会乞怜般地看着你。不知道他已坐了多久了,也不知道他乞讨了多少硬币?这样的场面
小时候过春节,母亲煮水饺,一旦有走水的,我们说煮“破”了,母亲就忙告诫我们:“要说‘挣’了。”我很疑惑,本来就是“破”了,干吗非要如此说?母亲告诉我,那样说会有败运,这般说就是发财。我心有所悟,但觉得母亲迷信极了,家庭的好坏岂是一句话就能影响或兆示了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一些认识不再单纯和极端。
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已经一天一夜了,这样的雨,总是给人无尽的感怀和遐思。雨从天上轻轻地柔柔地飘下,落在门前的台阶上,又沿着台阶流到地上,积起了一汪小水潭;雨滴也不吝啬地滴在上面,溅起一圈一圈的涟漪,柔柔地漾开,一波又一波,好似杂乱无序,但看久了,一点也不觉得的,相反却倒别有一番韵致。也如我纷乱的
外祖父去世十七年了,我没有任何的作为于他,没有给他烧过一张纸,没有给他的坟头添过一抔土。我知道外祖父在天之灵有知,是不会责怨于我的,但我无法给自己一点宽恕,这种负罪般的心境其实也不是任何做事可以免去得了的,只是生者负担的一种暂时减缓而已。我也并不想减轻自己的,我总希望他能够在我睡熟的时候一次次地来到
国人之中,对于麻将,几乎无人不晓。据说是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为了解决随行船员、水手、将士们航程的无聊和疲惫发明了这一玩意,没想到发明之后很快流行开来,这怕是郑和始料未及的。随着麻将极易地为人接受,它的味道也有些改变,好像不沾染上点钱,不搞一点“赌”资便不是麻将了,这确实有些扭曲人家的当初之意。
一九八六年,我考入了一所普通高中,同时来到这所学校的,我们乡镇一共十四个同学。那时的高中招生少,就连我们考初中也是学习成绩好的才能读,一来家里不渴求读书,二来如果不断留级复读是很丢人的事情。只有一口气一级不留地考下来的,才是大家最佩服的聪明人,而今天几乎消失了这种情况,倒是复读的人更能体现出价值,我
我家养过一次狗,那只黑狗仔不是买来的,农村人如果喜欢这样的动物,或者用来看门,邻居家有狗生产了,向人家随便要个狗仔是很简单的事,我家的这一只就是大哥向他的好友要的。那只全身黑棕油亮毛的小狗,刚出满月,就离开了妈妈,来到了我家。它生得肥胖结实,虎虎的样子,很逗人可爱。只是我家并不富裕,所以待小狗也没什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时遇到的一件事,这件事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可时至今日我心里仍旧无法轻松,无法忘记小女孩那深情地恋世和充满信任的眼神。二十二岁那年,我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乡下的一所初中代一年级的班主任兼数学教师,因为和孩子们的年龄差别也不是很大,加上农村的孩子早熟,我自然便成为学生们仰慕的对象,
这是一个朴素的家庭,几乎没有什么浪漫。妻子在机关单位上班,作息很有规律。丈夫在一家工厂工作,经常倒夜班,晚上下班到家时都是十二点半,很准时。丈夫之所以这样,是他不敢在路上耽搁,他并不是“妻管严”,他怕每耽搁一分钟,妻子就可能多焦虑一分钟。他也不想打手机,本来没有事,半夜三更电话铃响,好像有什么大事似
在懵懵懂懂中就告别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做了父亲。初为人父,一份欢喜备至,又一副忐忑不安,我知道这是一场很严格的考试,时间长,题目难,没有现成的答案,而我只有无可选择地去做好它。小儿体态发胖,于幼儿来说,些许的胖是一种可爱,别人的话虽很多的当面客气,父母看自己的孩子美却是普遍真理。小儿的胖在于胃口好,从
一“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面对这样噎人之语,任何一个懂点分寸的教师也不再说话了。谁为这句话辩解只能说明自己的不行。但不知,这句话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我们吃过多少这样的亏啊,怎么还是不明白任何绝对的东西都不是正确的道理呢?在今天,这样的话还能冠冕堂皇地盛行,真有“文革”之遗风。
人的一生总会有许多的不完美,不管是人为的,还是上天注定的,总之是我们不可补阙的,常常是只有听从命运了。虽也谙悉此理,等轮到自己,也便难以释然的。我自以为是一个珍爱生命的行人,而不是匆匆的过客。我试图凭借真本事改变自己周而复始的简单的没有任何波澜的职业,于是我用去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刻苦努力,去拥挤着C
父亲和母亲都快七十岁了,是地地道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就一直很少说话,既便少有的交流,也不是心平气和,而多是父亲充斥着的火药味。我总以为父母那一代是没有爱情的,无非是父母之命不得已走到一起,再后来是由于孩子的缘故又不得已呆在一起。他们那一代人真是可怜,苦着自己,跟一个并不能让自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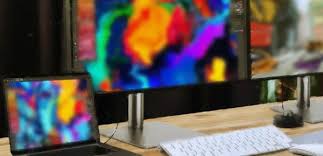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