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二狗背着粪筐,从碌碡门前经过,看到碌碡正坐在门口的一堆砖头上捧着碗喝粥。“碌碡,你怎么在家喝粥?细头没请你去吃酒?”二狗感到奇怪。“吃什么酒?”碌碡问。“你真不知道?细头那孩子今天满月哩!”“满月?”碌碡愣了愣,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是该满月了。”“他凭什么不请你?这老啬头他过河拆桥哩!”二狗有些愤
在我刚调到县城工作的时候,我度过了一段比较艰难的日子。新单位工作难度大,矛盾多,每个月都要为职工工资而发愁,加之单位没有宿舍,妻子也未能进城,家仍在原来工作的小镇。每天上下班,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奔波数十里,太阳升起时出发,太阳落山时归家。即使刮风下雨,也只能如此。那时,我的女儿才五六岁,在小镇的幼儿
我们弟兄几个从小就都掌握了一门技术——编苇箔。编苇箔,在我们老家土话叫轧箔子,轧,就是编织的意思。箔子也即苇箔,是用芦苇和草绳编成。芦苇一般筷子粗细,编织前要先把苇叶剥去,露出又黄又亮的苇身。草绳则越细越好,但要有韧性、不易断裂,用稻草或茅草捶熟后手搓而成。一块宽不到两米的苇箔,要放10多根经线,经
生活中,吸烟的人可谓多矣,戒烟的人也可谓多矣!然而,大多吸上瘾的人,要想戒除都感到殊为不易。有的甚至认为自己这一辈子都要与烟为伍了。我曾经也是这样一个人。我有过整整7年的吸烟史。我好烟,爱烟,嗜烟,7年里的2500多天,我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烟。每天早上出门,首先检查的是兜里有没有烟;坐在办公室里,只
从小,我就不是一个讨喜的小孩。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我打碎过家中好多个碗盆,就是放在高处的东西,有时也会被我爬上去拽下来摔得粉碎。因为这,妈妈骂我“讨饭货”,甚至还打过我多次。尽管我不知道“讨饭货”是什么意思,但妈妈那虎着的脸、高举着的巴掌还是把我吓得大哭起来。我就在这哭声中长大了。我背着书包上学了。
对于过去年代里的乡村孩子来说,劳动是暑假里的功课。我的暑假几乎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八岁上小学一年级。记忆中从上学始,每年暑假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挑猪草。那时每家每户都养猪,生产队里也有养猪场,因为粮食紧张,人都不够吃,不可能有粮给猪吃,猪只能以草为食,杂拌一点麦麸、米糠里面,
我的双眼被刺痛了!眼前,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脖子上吊着一个写满字的牌子,双膝笔直地跪在地上。她低垂着头,几绺纷乱而发黄的头发遮盖着黑瘦的脸庞,单薄的衣衫在寒风中瑟缩。牌子上写着“家中遭灾、无钱上学、请求好心人支持”的字样。从她身边走过的人司空见惯,少数驻足观看的人,也只是摇头叹息一番,然后快速离去
姐妹俩在小城开了一家发屋。发屋开在一条小街巷边。就着一家单位临街的围墙用石棉瓦搭成的简易棚子,内部用扣板吊了顶,墙壁刷了白涂料。上面贴着各种男女发型的画片。朝外的是两扇铝合金推拉门,门口竖着一座活动灯箱,上面四个字:姐妹发屋。姐姐老实敦厚,圆胖脸,细眼睛,白白净净,性格内向,不多言多语,只顾埋头做活
那次,厨房的下水道阻塞了,我用吸子吸了好久,可不仅未有效果,相反一点水都不流了。正是夏天,又到了晚上,我急得满头大汗。没办法,只好到楼道上张贴的小广告里找了个疏通工的号码,电话一打,对方答应马上就来。一会儿,来了一位四十七八岁的师傅,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上长满络腮胡子。手上拎着疏通的机器、弹簧等,一
H君是我在文化站工作时结识的。之后,他就成了我的学生、同事、朋友。那时,文化站缺少一个画画写写的人,有人介绍了H君。第一次见面,感到是一个挺文气、也挺帅气的小伙子,高中刚刚毕业,差几分没考上大学,正闲在家中,想外来锻炼锻炼。我喜欢上了这小伙子,他也愿意在文化站干。从小他就爱写写画画,能到这里可以说是
郑二呆子是个玩气功的。郑二呆子,既不行二,也不呆。因年轻时身体壮实、有力,只知呆做,不会耍奸,人送绰号“二呆子”。后跟随一家把戏团谋生,学得一手硬功,回来自己领头搭了个班子,索性以“郑二呆子”挂牌。久而久之,远近闻名。人们倒很少知道他的真名了。旧社会玩把戏的江湖艺人其实日子过得很苦。有一年除夕夜,郑
“瞎子笛王”姓朱名笛。本来,父亲给他取的名是“頔”,但这个字有点僻,不少人认不得,常常读成“由”或“页”。他就自己作主,改成了“笛”。那时他的眼睛还没有瞎,正对笛子产生了兴趣。他家的隔壁是剧团宿舍,每天早上都有一个人天刚蒙蒙亮时就站在天井里吹笛子,那声音像清风流水,脆亮圆润,好听极了。每次,他都是在
老家出了几桩腐败案,先是红极一时的某集团老总被逮了,接着是已升到市里任职的原党委书记也栽了,后来又听说某某被“双规”了,某某主动交出受贿的钱物了,一时似乎“洪洞县里无好人”。一日,母亲从乡下来城里看我。吃饭的时候,母亲跟我谈起这些事情。母亲说,这段时间老家谣言可多了,有说要对所有镇领导、单位负责人进
老家有一条小河,南北蜿蜒十多里,岸边垂柳似烟,翠竹成林,悠悠碧水,潺湲北流,来往舟船,帆影翩翩。两岸人家,临河而居,清晨或者傍晚,常常可见穿红着绿的闺女少妇在河边浣衣,捶衣声伴着欢笑在水上飘荡。每当夏季来临,清澈的小河便成了人们的天然浴场。劳累了一天的男人们,赤裸着身子,跃入清流,尽情洗濯,除去身上
她叫田思思,在J市文化馆工作了整整10年。她有一个不太雅的外号:小田鸡儿。这个外号是她的同事为她起的,虽不雅,却很形象,很贴切。首先是她姓田,思、鸡又谐音,其次长得又瘦小,再者她所从事的工作是舞蹈编导、表演,一天到晚蹦蹦跳跳,不是个小田鸡儿是什么?她听到后并不生气,知道是大家跟她开玩笑。时间一长,叫
母校白米中学于2008年12月28日举行50周年校庆,我应邀参加庆典活动。虽然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然而,当我冒雨走进这座久违了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上个世纪的1976年9月至1977年7月,我在这里读高二并高中毕业,两年后,我跨出师范校门又被分配到这里做教师,直到1
只要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没有谁不知道麦田,没有谁不喜欢麦田。没有谁的童年不与麦田有关,没有谁没有从麦田里得到过快乐。春节过后,天气渐渐暖起来,麦子趁着春风春雨,一个劲儿地往上生长。今天还看得见地里的泥土,麦苗还稀稀疏疏的,转眼就变得密密匝匝的了。过不多久,那成片的麦田就会窜出有半人高,乡村就成了麦
这条路,一头连着我的老家,那个叫竹园垛的小村;一头连着外面的世界,那个有着宽阔的公路经过的繁华的小镇。这条路,我走过若干次,当它还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时,我走过;当它变成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时,我更走过。哪儿有道坎,哪儿有个墩,我清楚;哪儿有株什么树,哪儿有朵什么花,我也清楚。闭着眼睛,我能骑车从这条
故乡有一条小河。喜欢静静地坐在那条小河边,看风景。春天,小河边的柳树爆芽了,长长的柳枝随风摇曳,冬天里被割得光秃秃的芦柴根,也冒出了一丛丛嫩嫩的芦芽,许多不知名的野草从泥土里钻出来,散散漫漫地把河边斜坡上裸露的黄泥覆盖出一片片新绿。岸边的一棵桃树,带着一身的粉红,立于水光草色之中,如处子般娇嫩、美艳
那个午后的蝉声,虽然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仍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在田地里冒着烈日的烤晒流了半天汗的大人们刚刚吃过午饭,正躺在树荫下休憩,轻微的鼾声从他们的鼻腔向外舒畅地发散。土屋里没有一点人声,爷爷钟爱的一只小花狗也无声无息地卧伏在草堆旁,眯着眼睛在打盹。家养的几只芦花鸡钻进了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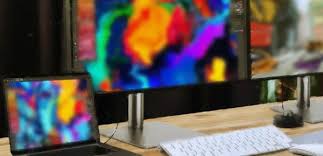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