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吵,很安静。肉身落地的一刻我自由了。我夹在人缝中,看见自己曾经漂亮的身体像滩鼻涕一样粘在地上,丑陋无比。我同围观的人群一样,摇着头,叹息着,然后走开了,就像早早去参观我画展的人们。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来聚在了我的墓地上,此后再不曾见过他们,除了紫琦和那个警察。我全程目送着自己的灵枢下葬,看着最后一掊土合拢。紫琦常来看我。我不知道我的死对她的打击有多大,她不知道我死的原因,但能接受我死去的事实。“我
“安当时也许被你的样子吓坏了,以为我叫你去杀她,她把我当成和她一样的人了。……我们其实都犯过错,也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抛开所有发生过的一切吧,我们今后要好好生活。”“你好好经营你的生意,我,你答应过送我去学画画,应该还没忘吧?”“当然。”“当我卖出第一幅画的时候我就正式娶你。”“那我就把我所有的朋友都找来,把你的画全都买光,而且每一幅都不许低于六位数。”“你可真是贪得无厌啊,六位数反正已经很多了,
这句“我知道”听上去像“我早就知道”。我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是紫琦的手指尖碰到了我的指尖。我本能的将手缩了回来,不仅是她,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紫琦紧闭着双唇看着我,好像又遇到了难题。“安,你也很了解吧,对她的一切你早就查清楚了,对不对?”像瓢凉水一样,我被自己的问题浇得清醒了,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样,不知自己的哪一根神经一闪念间转错了或转对了方向。紫琦依旧看着我,
“你不是来杀我的,你来到底想干什么?”……“别得意的太早,你们没有证据。”……“你不会是真的爱上她了吧,她大得够作你老妈了!”……“艾卡现在在哪儿?”“在他该在的地方。”“你不会把他杀了吧。”“你认为我有这个本事吗?”……“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直觉告诉我再去一趟老别墅会有所收获。斑驳流动的树影映在车窗上,像女人零乱的发丝,让我感到不快。车子飞快的行驶着,全速奔向城市另一端。我到达别墅后在每个
“我,艾卡,还有我先生,我们三个人本来过得很幸福,我给了我先生一个幸福的家,我是个守信的人。可有一天,我先生带我去拜访一对夫妻,他们是我先生多年的朋友,而且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说开始他们以为自己不生育,于是在四十岁上收养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男孩儿,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儿……我能听出他们欣喜之情。接着,在收养了这个小男孩不久之后,那个妻子就怀孕了。小男孩儿过两岁生日的时候,他们的女儿降生了,这对夫
她瘫倒在地上,像摊烂泥一样,显然已经筋疲力尽,胸脯一起一伏着。我准备起身离开时,她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指,抓得很紧,眼睛却直视上方,不知在想些什么。我把手指一根一根的从她手中挣脱。然后起身整好衣服,便离开了这里,不知道我的脚步声会不会刺伤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可以借助摄像头一遍一遍的反复欣赏我们俩刚才精彩的表演。而我当时却把这一点全然忘记了。有人说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当用下半身思考时,真正的
别墅在白天常常是空着的,天不黑这里不会有人,但监控系统24小时运行。但这也不难解决。我在确定周围一切安全之后,切断了电源,撬开了门锁,进入这座绝对时尚的水晶宫一样的别墅。面向大海的方向全是通透的玻璃。临窗而立放眼望去,那份豪迈和大气不是拘谨古典的乡间别墅所能比拟的。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这时似乎少了点什么。大小家具包括隔墙在内都以金属和玻璃为主,让人觉得冰冷,而且好像那些东西不太结实,一碰就会碎。别
警局已经立案了,他们在车里发现了炸弹的残骸,是一种很先进了热感应炸弹。在有人接近车子一米以内开始起动,30秒内爆炸,就是说,如果小丫头当时不发动车子也就还能多活几秒钟。紫琦被打了镇定剂,由阿姨看着睡得正沉。我租了辆车,径直开到了郊外的别墅。把停在车库里的那辆车上的某样东西拆下来,跑到车库外,扔得远远的。虽然有心理准备,还是被震得趴在了地上,我用拳头锤了下草地。我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举动有多么危险,因
谁说20分种上主路,20分钟还没走到庄园门口,从这儿开始又走了20分钟才到了主路,早有一辆的士等在那里了,远远看去是阿姨坐在里面,我也没打招呼直接开了车门坐进去。车开到峡湾桥上,我们下了车,打发走了的士。这地方是我选取的,因为阿姨要找一个方便谈话的地方,这儿最公开也最私密,再合适不过。问题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问才好,不如耐着性子等着她老人家自己慢慢说吧。“没想到你这小子还真能沉得住气!我还真小看
大片的绿地,灌木,稀疏的树林,湖泊,还有午后的阳光。还有我们俩。我们手拉着手,像初恋的情人。她的手细腻柔软,让我心底涌起一层暖暖的温柔。当时她36岁,我23岁,小她13岁,但多数时候我根本记不起她的年龄,她又像姐姐,又像妈妈,又像爱人,又像一个小女孩儿,在我的眼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她的身份证件,根据上面的出生日期,她当时应该是42岁才对,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很淡然的说:证
我走过去坐在她腿边,从她手中拿走那正燃着的烟头碾灭在烟缸中,而她夹烟的手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她在看着我,目光木然。我转过头迎着她的目光。我发觉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发觉她的意志可以被轻意击破。我伸出手臂,几乎在同时,她蜷起膝盖,将头向前倒在我怀里。就像在昏睡中她抱着我的头一样。当时她轻轻地吻着我的额头和脸颊,现在,我吻着她。我们这样互相依偎着,在沙发上度过了别墅中的第一夜,什么都没有发生,两个
我拎着我的布袋子,虽然那里面空空如也,但那是我唯一的有形财产。我站在一段跨海桥上,它下面是一道窄窄的峡湾。峡湾一头伸进城市的陆地深处,另一头则像开口的喇叭一样,在远处扩展成辽阔的海面。我靠着栏杆站了很久,看向最远的天海交界处。天色是灰的,海色也是灰的。天海交界处浸在一片迷雾中,我什么也看不清。我无数次的看过手里的那张支票,那个具体数字我现在已经记不很清楚了,只记得那笔钱至少足够我躺着吃上一年的。我
怕倒没有,不过真有一点点意外。她带我去看了她的报社,杂志社,私立学校还有健身中心。她告诉我,她还在一些大型的房地产和金融公司占有相当的股份,她不须对后者操心,只是分担风险,坐收利润。她每次去看的,只是些她自己的产业,须要她亲自的决策和操持。但我现在也看到她是怎么管的了——一天去一次,每次一小时。我想十有八九也就是开开会看看景而已。我跟在她后面,随她各处参观。所有的人对我都很尊敬,走到哪里总有人一路
啊,我上头版头条了,是一幅我戴着墨镜的大照,下面注着:林奇的小男友。再往里面翻,竟然占了好几版,图片不少。我仔细端详了那些图片,从各个角度看,我发现自己还是蛮上镜的,早知如此,当初不如去混个演员当当,说不准还能成名呢。我知道这份报纸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林女士看到的,于是草草翻过后便把它压在了自己房间的枕头下面。已经几乎是下午了,林女士的房间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我那一整天几乎时刻守在她的门外,随时听候调遣
我不是一个坏人,但也确实算不上一个好人。而此时林女士肯定认为我是一个杀过人的凶手,她还敢把我留在身边,这个女人也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叫什么名字,这么久了,只知道她姓林,连名字都不知道。还有,她到底是做什么的,她这么多钱是哪儿来的?她是个高级妓女吗?以她的年龄应该不会。那么她是犯毒的?是黑社会的?是什么有钱人的侧室?我实在猜不出来。她也曾经提醒过我:你不要费力的去探听我,对一
当天下午我就随林女士乘飞机飞到另一座城市了,对我来说这时间并不仓促,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就一个包而已,这包里的东西当垃圾扔了估计也不会有人拣。我透过飞机的弦窗望出去,夜幕下是一片无边的灯海。后来我才知道,这座城市是从来不睡觉的,在夜晚。林女士有两个住处,一处在市中心,一处在郊外。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市中心那44层高的顶楼上,整个那一层都是她的,和楼下其它各层的结构不一样。临东的大房间是她的起居室,
我吃饱喝足,倒头便睡,睡到半夜忽然醒来。我一动不动,只转着眼珠看着周围的一切。宁静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洒满整间屋子,在这华丽的居室中,我感觉自己上了天堂。虽然我也没见过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想象中应该是个无比舒适的地方。以这个标准衡量,这里就是——天堂。我是男人,男人不怕失身,管它的呢!我又闭上眼睛,整整枕头,一觉天亮。我睁开眼的时候,看见白色的枕套上有红色的血印,我以为刚醒眼睛有点花,到了洗手间才
是的,如我所说,这一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只是下意识的转过头,看见大约十米外的一个破旧的木制长凳上坐着一个女人。那女人看上去年龄应该不小了。真失望,我本来期待见到一位美女,至少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我长相不差,又善于打架,对无知少女有致命的吸引力,也许会从这个偶然的相遇发生一段浪漫的故事什么的。唉,谁知是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我又转回头。没什么可看的。她不仅上了些年纪,而且包裹的很严实,穿着高领的长
退伍之后,我本来想找个像样的工作,让生活安定下来。我知道我不小了,人一过了二十岁,便会想到可能随之而来的各种事,结婚生子,安家落户,干活赚钱,什么什么的……总之,先把钱赚到手,然后,嗨,安定生活。我承认我并没有十分地认真的考虑过一系列富有责任感的问题,但考虑过是真的,就算是随便想想吧。我右手夹着烟,左肩扛着包,头发又长又乱挡住了我漂亮的眼睛,还有我那身衣服,个性跟主人一样,肥肥大大,踢踢遢遢,我不
我当时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人比我更倒霉,三岁不到时,因为一场争执,父亲失手杀死了母亲。也许注定我至少要失去他们俩人中的一个,因为当时母亲发了疯,她手里拿着水果刀,向父亲扑来,就那么一瞬,母亲倒下了,父亲手臂流着血,瘫坐在地上。从那一刻起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娘的孩子。很快,连爹也没有了,有人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了。你知道为什么,不用我解释。这种家庭纷争,谁也没法把它说清,更何况父亲什么也不肯说,只有一句:你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起点读书如何开启横竖屏切换-起点读书开启横竖屏切换的方法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心遇如何删除账号-心遇怎样注销账号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破晓传说所有文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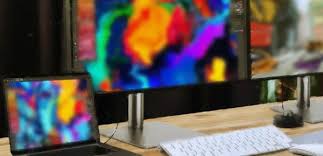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procreate怎么提高清晰度-procreate如何提升清晰度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无尽梦回BUG之梦强度高吗-无尽梦回BUG之梦技能强度测评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摩尔庄园别人访问记录查看方法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放置勇者传2属性攻略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方舟健客网上药店如何清理缓存-方舟健客网上药店怎样清除缓存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原神如铁鱼般破障怎么玩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
另一个伊甸洛基德介绍